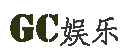濮存昕:轻舟已过万重山

回想起第一次到济南,那是在1972年,他怀揣着对未来的迷茫和希望报考文工团,结果是悻悻而归。40年过去了,他带着自传《濮存昕:我和我的角色》与泉城读者见面,轻舟已过万重山。
写书这件事不是必修课,但在濮存昕眼中,时间就像流沙,写一本自传于自己而言,是一件“来得及做的事”。媒体、观众、读者有数不完的问题,每回答完一个问题,他会嘴角上扬,自言自语一句“胜利啦”,笑得像个顽童。在他的讲述和自传里,大家得以走进他的内心世界,感受他对艺术的敬畏和热爱。
成为演员
濮存昕是“星二代”,年轻时候的长相是妥妥的“小鲜肉”,如果放在现在,濮存昕这样的人一定会被视为“老天爷追着喂饭吃”的天之骄子。
可濮存昕一开始并没有拿到大男主剧本。父亲苏民曾经是北京人艺的建院元老,当过导演、演员,濮存昕从小在人艺大院里长大,对舞台一点也不陌生。但是他幼年得过小儿麻痹症,长大后又离开北京,在黑龙江建设兵团当了近8年知青,重回北京加入空政话剧团9年后才重回北京人艺,绕了好大一个圈,碰过无数次壁后,回到原点。人生的每一步路都不会白走,后来他演话剧、影视剧,演艺道路越走越宽,濮存昕在书中用了很多笔墨来回忆那段苦日子。他说,“对任何一个人而言,从学校毕业之后走向社会的第一步,都是最值得记录的。”
濮存昕的知青生活从16岁开始,当时的他懵懵懂懂,好像只是去一趟远行,离开了他从小生活的北京,到了黑龙江,去玩,去保家卫国。
热情随着时间被冲淡,他开始想家了,但是北京户口已经销了,他有家不能回。濮存昕想过很多门路回北京,考文工团一次次失败,希望的火苗一次次被掐灭。那段日子,充满着激情,也弥漫着对未来的恐慌。
对待这段人生的“弯路”,濮存昕心怀感恩。他说,父亲眼中的他,最大优点是责任心重。不管干什么事情一定会尽可能干好,哪怕是违心的,只要应了就得做,做就要做好。这种品质其实是在黑龙江当知青时练就的,“那个时候要割麦了,你肯定得割到头,你不割完,到时候别人给你割,丢不丢脸?和你一个班的同学一起坐火车去黑龙江的,他们还在干,你看什么?”
在黑龙江待了7年半,濮存昕对家乡的思念与日俱增,一起增长的还有与生活对抗的能力,每每回忆起,或与曾经的知青队友重逢,他都会忍不住感叹,“16岁到24岁,给予我们能够稳稳当当地做事情、老老实实活着的能力,那段生活很重要,苦得不能再苦了之后的生活你就不在乎了。”
但濮存昕又是幸运的,一路上他遇到过很多贵人,赏识他的才华和努力。他说自己是一个有福气之人,在人生中非常重要的转折点上,都有人在帮他。
在空政话剧团当了多年部队演员后,濮存昕仍然挂念着人艺,但以父亲的性格,绝对不会为了儿子说半句话,更不会走后门。后来是前辈蓝天野,借调濮存昕来演《秦皇父子》,为梦寐以求回人艺的濮存昕打开了一扇窗。蓝天野主动找到了濮存昕,还拉来了王贵团长,要一起培养这个年轻人。到人艺后濮存昕就笃定,这是他“咬住青山不放松”,来了就不走的地方。
濮存昕的讲述娓娓道来,从侧面折射出新中国表演事业的发展进程,中国演艺事业中一座座“大山”式的人物通过他的视角被还原出来,他们是那么纯粹、那么可爱,曾经的演艺圈是那么晴朗。父亲苏民曾因业务上的分歧与当时的人艺院长于是之先生闹了矛盾。然而,于是之并没有因此冷落濮存昕,还力荐他演了李白。在濮存昕的成才道路上,王贵、蓝天野、英若诚、林兆华等人艺一代代前辈们的提携都功不可没。
学艺先学德,做戏先做人。真正地生活过,过过苦日子,也见过真正的大家。成名之前的日子为濮存昕铺就了人生永恒的底色,永不自满、追求更好。
自学成才
上完六年级后,濮存昕就没有在课堂上再学知识,后来他能成为表演艺术家,还有机会出书,很大程度上都是自我勉励,把社会、舞台当课本,自学成才的结果。从回归舞台,他以继承老一辈艺术家的优良传统和人格风范,坚守对戏剧艺术的赤诚热爱,坚守艺术的理想、戏剧的品格,40多年的磨砺,成为新时代艺术大家的典范。
演员一定要多读书、会读书,濮存昕一直践行着。
他下乡时所在的团部,图书馆的门可以“随意进出”没人管,给他提供了便利阅读环境。“那时候已经没图书馆了,原来老农场留下的图书馆,一扒拉,锁就掉了。”那些书为离家在外的濮存昕提供了精神食粮,抱着“解闷”的想法,读了很多在后来看来尤为重要的书籍,为他的表演事业提供了养分。
至于读什么书,濮存昕说,“应该看那些和自己没关系的书,而且越多越好,你必须参照太多的事情,没准你一下就顿悟了,想不明白的事儿明白了,绕不过去的弯子、钻不过去的牛角尖儿,就过去了,起作用的就是这些杂学,一些反面的东西。”在他看来,学习这件事对于一般的学生来说,只会完成任务式地一堂课一堂课地去考试,而对于真正的好学生来说,一定是能够把所有的课连在一起去联想。
好书要反复读,濮存昕说现在当导演导的戏都是过去曾经演过的,再重新读剧本,才发现原来都没理解,所以重读经典是他60岁以后在做的事。这次出门,他就带了鲁迅的书,“要重读、复读以前看过的好书。”
演过李白,也读过很多诗,濮存昕也从中汲取到养分,在他心中,中国的词句,中国的语言和文字真的妙极了。“读这些诗的时候,其实我们在体会灵魂与先贤们对话,在文学中间,我们可以互相参照,客观的空间和自我的空间,我的空间和他人的空间。”
“文学艺术看似是无用之学,但是它给予了生命更高的品质。”濮存昕说演员走到底拼的是文学素养。在他心中,真正的演员不是在导演和镜头的帮助下完成表演,表演专业其实是形象文学专业,台词不仅仅是台词,还代表了所思所想,“如果脑后无光,只是台词和台词,只是表面的东西,就不是有思想的语言,它只是别人的语言,附着的是一般人都会有的情感、情绪。而形象的文学,不能失掉文学性,所有的艺术不能失掉文学性。”
焦菊隐先生在未完成的导演提纲中说过的一句话对他影响很深——“与观众共同创造”,濮存昕曾在不同场合提起过这句话,“我们一定要知道,在创作角色的时候、创作形象文学的时候,和观众一起去探讨,探讨这部作品所能够给予台上、台下的共情、共鸣。”
没有最好
“我是通过阅读慢慢知道自己,因为我一直是不成功的演员,30多岁没人理,我出道太晚,起跑线太靠后了,人家起跑线都在前面,但是还好,好在遇到很多能帮助我,遇到很多机会,我都没浪费。”
更多的阅读体验来源于剧本,来源于演的角色。在话剧舞台和影视剧中,他是孙策、哈姆雷特、李白、李尔王、鲁迅、弘一法师……多年过去,那些他诠释过的角色早已和人生相互渗透。演完《哈姆雷特》,他曾留下一段话,“像离开狭窄的闹市,走进无边的原野,我享受到了自由,同时又体味到了艰辛。”成为哈姆雷特的过程,酣畅淋漓,过瘾极了,幸福极了,他感谢哈姆雷特,让他在台上表达出了现实生活中不曾表达出的觉醒,发现了自己都未曾发现的天性。经历了这么多,感悟了这么多,人生是不是就没有遗憾和残缺了?当然不,但可以坦然去面对。
濮存昕曾两次出演《雷雨》,年轻时演周萍,年龄大了又演周朴园。演周朴园的时候再去看《雷雨》的剧本,视角和内心世界已经截然不同,为此他带着所有演员又重新翻开了1934年的版本,在其中找到从未发现的伏笔以及全新的主旨。
他承认,即便到了70岁,他依然没有到达前辈所及的高度,调侃自己“我不是站在他们的肩膀上,我还没有爬到他们腰。”但他不否认,是真诚让他跟前辈们站在同一条起跑线的,“那个起跑线是什么?就是你质问自己是不是真诚,如果你是真诚的,你永远和你敬仰的前辈们站在一个地方。”
表演的初心是什么?濮存昕用大白话回答,“你不让我干,不给我钱我也干,我就想演。小的时候因为我不出色,我不受待见,但是参加诗歌朗诵的时候,一个人站在台上,演得不好,别人也鼓掌,成就感是那时候生发的。”
在他心目中,一名好演员应该追求审美的三个层次:看—赏—品,为的是让观众的闲情觉得值,观众时间很宝贵。
在谢晋导演的电影《清凉寺钟声》中,濮存昕曾饰演明镜法师,为寻找角色感觉读了《弘一大师传》,也埋下了后来出演弘一法师的种子。濮存昕演活了弘一法师,也把弘一法师的名言“去去就来”刻入了自己的生命中,内化为自己的人生态度。
“轻舟已过万重山。”他形容生命如同长江之水,到他这个岁数长江已经过了南京,很快到吴淞口,可以望见汪洋大海,“没有选择了,就好好喘气就行了。”生命是一场轮回,河水被太阳蒸发变成水汽,又回到喜马拉雅山,变成水滴,再从三江源流向大海。所以弘一法师说“去去就来”,“也许来,也许就不来了。”说这话的时候,濮存昕是笑着的。他感叹一辈子太短了,“顾不上那些羁绊我们、影响我们往前走的事情,来不及生气,来不及争吵,赶紧做事情,这本书是一件来得及做的事情,做完就完了。”
69岁的最后一天,濮存昕在济南看完了泰山对国安的比赛,如他所愿,泰山赢了,他用大半辈子都在超越自己,如今更和时间赛跑,“没有最好,只有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