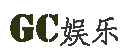新确认7名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者 她们何时能等来道歉?
【新确认7名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者】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工作人员在湖南新确认7名“慰安妇”制度受害者:97岁的雷金二(雷金安)、92岁的雷金莲、85岁的易菊连、107岁的李淑珍、98岁的阳奶奶(化名)、99岁的姜奶奶(化名)、99岁的李秀青。她们曾遭非人对待,她们还在用余生等待道歉。受害者在世人数越来越少,寻访团队一直在和时间赛跑。勿忘历史,珍惜和平!(总台记者李筱图片来源:南京报业传媒集团)
相关:
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者陈连村去世:主动揭露伤疤,没等来道歉
人生的前半程,陈连村没有多少机会选择。
1940年,14岁的陈连村被侵华日军强征到海南保亭县加茂据点修路架桥,做苦力、遭毒打、忍受轮番蹂躏,先后被抓走至少3次,最后躲进山里,直到日军投降。
人生的后半程,陈连村选择成为勇敢的人。八九十岁时,她出镜关于“慰安妇”的纪录电影《二十二》,远赴北京、上海、南京和韩国首尔参加社会活动,一遍遍流着眼泪用黎族话控诉,要求侵略者谢罪赔偿。
现在,她安息在自己挑选的长眠地,周围的热带林木翠绿繁茂,景色在当地最平常不过,但她喜欢,这总归是自家地。
据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消息,2021年6月30日凌晨5时许,侵华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陈连村老人在海南万宁逝世,享年96岁。至此,海南省公开的“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仅剩两人;上海师范大学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登记在册的中国大陆地区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为14人。
2020年10月5日,陈连村坐在家门口。海南“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情况调查志愿者陈厚志供图
“我已出尽力气但无济于事”
2001年元月六日,海南“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情况调查志愿者陈厚志录下了陈连村的第一份受害者口述。
在这份口述里,14岁的陈连村和几个姐妹一起被日军强征去修路。因为工效低,日军经常惩罚她们做“四脚牛”——四肢张开,拇指、食指及大脚趾点撑在地面上,腹底立着锋利的军刀,背后有棍棒,一旦顶不住,便会遭到毒打。晚上,她们就睡在劳工棚里。
日军逼迫陈连村参与修建的加茂大桥。海南“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情况调查志愿者陈厚志供图
一天晚上,陈连村被汉奸叫出工棚,守在外面的日本队长的亲信说要带她到河边捉鱼。刚到桥下,日本人便将她推倒在沙地,压住她双手,捂住她的嘴,陈连村在口述中说,“我已出尽力气但无济于事,还是被这个畜生奸污了。”几天后,陈连村感到下腹像被火烫一样疼,全身无力,但日军仍三天两头强迫她,她几次逃跑,又被抓回毒打,直到遍体鳞伤、面黄肌瘦,才被日军赶回家。
母亲看到女儿回来,抱住她大哭,又托人煎草药给女儿治疗。身体刚见好转,汉奸又找到陈连村,要把她带回据点。母亲哀求,汉奸威胁说不回去就放火烧村,把村里人杀光,陈连村只好跟着回去。
这次回去,她如玩物一样被日军带到其他据点,再带回来,被囚禁在木板房里任人施暴。陈连村偷偷逃跑,又被抓回,小腹痛得直不起身,但她不敢反抗,直到找机会再溜出去。
这次,陈连村没敢回家,母亲把她藏在距村子一公里外的小山包上,找人挖草药治疗,一个月左右,听到没人进村抓人,陈连村便带着草药回家,但不久又被告密。来不及逃跑,母亲叫她躲进装稻谷的竹编筐里,躲过一劫。日军走后,陈连村又躲进山里,再也不敢露脸,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
往后的日子里,陈连村想起这些就后怕,经常深夜从噩梦中惊醒,伤痛连绵。
2018年3月9日,陈连村在韩国首尔参加控诉日军暴行的活动。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供图
一生伤痛难愈
“日本兵”成了陈连村的禁忌。
志愿者陈厚志说,一讲到日本,陈连村就紧张起来,不停地眨眼睛、掉眼泪。这份口述断断续续做了一个月,大部分时间,陈连村都在哭,甚至哭得很大声。有时说到敏感处,她就停住直摇头。
晚年,陈连村与小儿子张先雄一家同住。一次采访中,张先雄说,陈连村看到电视上的抗战剧,依然会觉得害怕,他只好把母亲卧室的电视搬走。新中国成立后,母亲在生产队干活,天黑后,她必须有人同路才敢回家,即便后来给自家菜地干活,也必定赶在天黑前回家。
除了怕黑,陈连村还恐高、怕声音大。有时陈厚志带着陈连村参加活动,需要走楼梯,如果不搀扶,陈连村就迈不开步;周围一旦声音太大,陈连村还会跳起来大喊一声。
照片里,陈连村总是裹着围巾或是戴着帽子。陈厚志说,这是因为老人总感觉头晕,她还总是干咳,这都是年轻时落下的病根。
2018年3月9日,陈连村在韩国首尔。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供图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员刘广建自2016年起,每年都会带队探望老人。有时还没等他们问起,陈连村就会主动讲起往事,但在日常生活中,陈连村从不主动谈论自己的经历。
去世前一天清晨,陈连村对共同生活了20多年的儿媳伍海珠说,自己肚子有点儿硬,很痛,小时候被日本兵打过,伍海珠这才真正知道陈连村的遭遇,也明白了为什么婆婆身体一向很好,但总是脚痛、腰痛、后背痛。
就连儿女们,也是陈厚志找上门来之后才知道的实情。
初次听闻母亲的遭遇,小儿子很同情,大儿子却有些接受不了。陈厚志不断解释,“阿婆是被逼迫的,我们应该理解阿婆,帮她把痛苦释放掉,不然阿婆就更难受了”,家人们才慢慢接受。
在陈连村的出生地保亭县,跟她有相同遭遇的,都被称作“日本的女人”,很多人觉得这事儿“不光彩”。
陈连村在自述中提到,“本地人都知道我的往事,觉得被日本人强奸过的人下贱,不敢正眼看我。”陈连村的侄女陈雯(化名)告诉新京报记者,小时候她一出家门,村里人都会因为“阿爸的姐姐”取笑她,“我连去学校都不敢说话,读书回来也是关门在家搞家务,不敢跟人家玩”,家里人也很少再提起。
这是老人们公开的秘密,侥幸活下来的人要么背井离乡,或者干脆埋在心里。1953年,陈连村与老家在万宁的汉族人结婚;5年后,夫妻俩搬到万宁居住。近几年,陈连村在保亭的弟弟去世,她的身体也不太灵便,很少再回老家了。
“多亏了政策和政府媒体的宣传,现在大家都不会议论了。”陈雯说。但据陈厚志统计,自陈连村逝世后,保亭县公开身份的受害老人已无人在世。
2016年10月,陈连村(右)与韩国“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李容洙出席中国“慰安妇”历史博物馆开馆仪式。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供图
站出来向公众展示苦难:“报道日本人做的事,我生活才会舒畅”
海南是侵华日军“慰安妇”制度的重灾区。陈厚志从事当地“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调查已有25年,仅他掌握的海南省公开身份的受害幸存者就有50多位。
2001年7月,黄有良、陈亚扁、林亚金等8名海南“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向日本政府提起诉讼,要求日本政府谢罪以恢复她们的名誉。但直至2017年,8人中的最后一位黄有良去世,也没能等到胜诉的消息。而此后接替她们不断申诉的,正是陈连村。
一直推动此事的上海师范大学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将陈连村看作是第二批申诉者的代表。她身体结实、讲话清楚、事实清晰,子女也配合,最重要的是,老人有勇气站出来,向公众展示苦难。
2016年10月22日,90岁的陈连村作为受害幸存者代表,出席中国“慰安妇”历史博物馆的开馆仪式,并为坐落在上海师范大学校园内的中韩“慰安妇”和平少女像揭幕;同年12月13日,出席了首部慰安妇题材电视连续剧《地狱中的女人》的拍摄启动仪式;2017年12月18日,包括陈连村在内的17人向中国外交部递交了外交保护请求书,请求中国政府行使外交保护权,为民间战争受害者讨还公道,要求日本政府尽快公开向受害者及其遗属谢罪、赔偿。
2016年10月22日,陈连村与来自韩国的“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李容洙出席“慰安妇”少女像揭幕仪式。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供图
据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志愿者记述,此时的陈连村因为肺炎,已住过三次医院,手上的皮肤也有些脆弱,10根手指都涂上了黄色的药膏。
2018年3月,92岁的陈连村在苏智良、陈厚志等人的陪同下,作为中国受害者代表,出席在韩国首尔举办的国际活动。苏智良明白,让陈连村一遍遍回忆过去很痛苦,他也在呼吁关注的同时尽量照顾老人的感受。但他能感觉到,陈连村很刚强,一直抱着要日本政府认错的基本立场,希望永久的和平,不要让悲剧再重演。
陈厚志知道,陈连村并非一直勇敢,他曾绞尽脑汁让老人再多吐露一点,反复劝她,“你是亲历者,只有说出来,才能让你们受到的欺辱给社会知道。”在镜头前,她用纸巾抹着眼泪哭诉,“报道日本人做的事,我生活才会舒畅,不然我就难受,日子没法过。”
但陈连村的仇恨并不指向现在日本人。她曾跟陈厚志说,他们没参加以前的战争,现在不打我们了,也不欺负我了,我不仇恨他们。
2017年12月21日,陈连村在北京控诉日军暴行。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供图
有人记得,她就高兴
丈夫是陈连村苦难生活的暂停键。
解放后,陈连村的丈夫从万宁来到保亭,宣传党的新政策,吸纳年轻人加入。在这里,陈连村认识了他、与他结为夫妻,但直到很久之后才敢坦白遭遇。男人从没“嫌弃”陈连村,她总是和陈厚志说,“这个人很好,我以前受过那么多苦,就是这个男人才能包容我。”
陈连村的孙女也曾对慰问的志愿者说,爷爷活着的时候,跟奶奶之间的感情特别好,从来没有吵过架,一次也没有红过脸,从来没问过奶奶过去的事情。两人结婚后,常往来万宁和保亭做些小生意,有时会在老家摆个早餐摊卖油条、糯米糍和凉茶,轮流招呼客人。
丈夫去世后,晚年的陈连村常常一个人坐在屋里粉色的塑料座椅上,或是躺在床上,天气炎热,就慢慢扇蒲扇解暑。儿子儿媳白天务工不在家,她就喂喂鸡、喂喂鸭,身体好的时候还能劈柴、削番薯,煮好饭等着家人回来吃。每年有三四次,陈连村会带上特产胡椒,搭两个多小时的公交车,摇摇晃晃坐到保亭看望弟弟一家。
熟悉陈连村的人都知道,老人格外爱干净,床垫、枕头、被褥一定要叠得整整齐齐,每晚都要冲凉,即使生病卧床也不例外。
不论是家人还是志愿者,都认为陈连村温柔善良好脾气。不过大多数时候,陈连村都很沉默,只有别人问话时才回上两句。伍海珠说,婆婆基本不去村里走动,偶尔有其他老人路过,才会扯着嗓子胡乱拉拉家常。
2009年,上海师范大学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右)、志愿者陈厚志(左)与陈连村合影。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供图
但志愿者到访时,陈连村总是很高兴,经常拄着棍子到大门口迎接。听不懂普通话,她就笑着等待“翻译”把陌生的音节变成能听懂的祝福。刚见到陈连村的时候,陈厚志总觉得她闷闷不乐,直到近几年看望她的人多了,老人脸上的笑容也多起来。
认识陈连村至今的20多年,苏智良每年都会请一两位志愿者来探望老人,定期送来援助,随时为老人报销医药费。“我们自诩代表民众关爱她,她就能够得到一些温暖,我们希望通过援助计划,不是加重她们的痛苦,而是改善她们的生活。”
刘广建希望她们能得到更多人的关注,“只要有人经常去看看她们,让她们感觉到关心,她们就很满足了。”不仅如此,刘广建认为国内对于“慰安妇”制度的研究也少之又少,受害幸存者人数日渐减少,很难再将研究推进。
2020年10月5日,志愿者陈厚志(左)最后一次见到陈连村。海南“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情况调查志愿者陈厚志供图
6月30日一早,伍海珠照例端早饭给陈连村吃,她看到婆婆躺在床上不说话,眼睛紧闭,眼泪从眼角一直流,叫她也没法应答。这天,她珍爱的亲人回来了,同村乡亲、陈厚志和两位上海来的志愿者也赶来送她一程。
除了她应得的道歉。
新京报记者左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