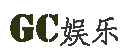乡戏李闽山:鲁西平原东南坡村的童年记忆与乡村文化
乡
戏
李闽山
我第一次看戏是在乡下的姥姥家,是鲁西平原的东南坡村,说不上是惊奇还是新鲜,反正很好玩。那时我在家乡读小学,眼里已没有了童真的透明, 拾起了要读懂一切的朦胧。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是机灵加笨,是聪明的傻,稍不留神就能把猪八戒的娘给气死,即使是在看戏,那眼儿耳儿也不是那么老实,像山狗保持着警觉。
乡村开戏是件大事,村民们早早几天就奔走相告,胜过狗剩他哥娶上媳妇!蹲在屋檐下围着地上的茶盏慢慢品的汉子们,嘴里吧嗒着烟,不到一锅子,就把将要上演的戏说出个八九不离十。盘腿坐在弄子里土沿上的姑嫂大娘们更是好生了得,她们就着夕阳,把鞋底拨开金色的明亮斜斜举起,慢慢用针把线引过锥子事先钻好的眼儿,一只千层鞋底二百五十个针眼儿就有五百句台词,五六个村妇围一下午,足可唠叨出一部乡村野史,而过两天要来的戏是这部野史的开篇。我想,自从有了女人可能就有了戏剧这门艺术,戏剧的主要构成是台词,而女人总能把它玩在嘴上,她们的伟大就在于把生命从婴幼哺育成人。

戏台是用白棒子桔梗捆扎起来的,台面是大伙把家的门板卸下来铺成的,中间的缝儿窄宽不一, 与唱梅林戏的“茅担抬白窟,扛到段中央,搭起戏台来,唱到大天光”大致相同。戏台中央上方用一根棒子橘挑起一盏汽灯,一场戏下来,一位汉子要上去打好几次气,这个活儿谁都愿上去干,这可是一个在明灯下能够显眼儿的活,哪怕是暂时的,也是暂时的灿烂,台下几百号眼睛会突然缠住他,特别是那些姑嫂的眼睛,可能其中就会送去一个机会。汉子打气时,故意放慢动作,完毕了又做了个回看台下所有人的造型,才不舍地离去,忽然,他又折回身稳了稳那并不晃动、不需再去扶稳的灯盏。我真想一脚把他从台上踹下去,假如能踹得动这位傻大个的话。本来这台上台下的戏就乱,他这样胡加“情节”真是乱中添乱!吕剧常常有激动人心的情节,何况是一出“铡陈世美”的戏,那铺垫起来的门板常常被跺脚震得“嘭嘭”作响,于是戏台摇晃起来,导致汽灯一闪一灭,台下会一明一暗。每每到暗时,台下也有了戏。激动的汉子会趁机朝身边谁家的嫂子胸前“闪击一把”,嗔娇的骂声此起彼伏:谁身上的家什呀?咋扔到他娘的身上啦?!那个电棒子筒往哪里照啊?!有本事掏出你那根小电筒给你老嫂照过来?!非扯了你去不可!
在叫骂声中,这边的电筒光束灭了,可那角旮旯里又亮起来了……于是四周响起各种年龄段的浪浪笑声。妙就妙在有些姑嫂们明明知道暗中伸过来的那只“乌龙手”或前或后,或左或右,却故意朝另一处喊骂去,还把手说成是“扔过来的家什”。还有的干脆把鞋子脱下朝一远处空地扔去:俺就知道是你,瞧老娘不打死你才怪呢!神态认真而夸张。能扔鞋的是声东击西的高手!反正大家是在暗处, 在暗处操作的东西都比较有趣,因为它是道德监管的一个死角。
看戏是乡民们的一件大事,谁都不愿落下。特别是在文化生活贫乏的年代,偶出一场“铡美案”, 更是热闹。乡民们淳朴,他们中很多人的目的不是去看戏,看懂和看不懂台上那些张牙舞爪一招一式的内容也不是主要的,关键是珍惜这个社交机会, 传递一下只有乡民们自己能读懂的信息,满足一下那渴求已久的声色,刺激一下爷们枯裂的疲惫。如果说台上的戏好看在情节上,那么台下的戏却妙在细节上。情节可以杜撰,可细节却是真实的,艺术的生命靠细节延续。

我更看不懂剧情,而且相信在场的那些“聪明的傻小子们”也一样对剧情朦朦胧胧,支吾以对。那些唱戏的用长马褂替代古装,用黑色的瓜皮帽替代哪个朝代的头饰,显得滑稽可笑。“陈世美”更是绝,下半身系一条围裙,上半身一件短褂,外再披一马夹,一只脚穿着绿色解放鞋,另一只脚套着一只千层底黑布鞋,两只脚在台上一上一下,绿色和黑色时不时地划过眼前,“陈世美”无规则的脚倒腾着戏的步子。真是美化不对负心郎而言。戏班子的头对村支书说:负心郎的衣服可以不统一、不一样,凑合更好。他说明一个理:品德不高的人, 无须注重他的表面。不过,“陈世美”脚上的那两种色倒是那个年代的完美色,谁说“世美兄”身上没有“美”呢?
懂事后,我又用另一种懵懂的眼光看乡戏,那是一种醉后的“眯缝眼儿”,像是欣赏一幅猜不透的毕加索油画。酒过六巡后,腾到七彩的浮云中, 我看到红成一片的傩舞,这傩舞是一段浓缩的世相。傩神们非常虔诚地祈求天地,而信仰又非常“虚幻” 地期盼人间的虔诚,人和天地之合则造就风调雨顺, 难道这不是生命所追求的最完美的神韵吗?红色的面具,红色的脑饰条,红色的裸臂,红色的胸膛, 红色的马裤,奔放出一团红色的旋转的火,疑是“丹霞众神”在舞台上旋动着韵律驱邪祈福。傩戏是天下最古的乡戏,你只能意会,不可解读,能解读的 艺术会搁置高柜很少再去欣赏。这个乡戏远比我鲁西平原上的“铡美案”要文化得多。不过对在台下看戏的那些村民们来说,纵然有什么“更文化的” 或是“更有思想意识的”,又有什么关系呢?在乡下看戏更多要的是那浓烈的乡土气氛和热闹劲,要的是亲朋好友、七大姑八大姨的熟面。
梅林戏已从乡村歇山式的土台上搬进了城里, 土戏已不再土,民间文化味已不断受到现代艺术的侵蚀。尚书第内电子屏幕下演员们的唱腔中,“道士味”已成为烹饪中吝啬的厨师勺里的味精胡椒面, 在台下看戏的人是真正地欣赏,那研读剧情和台词的神态显得专注而孤独,那戏的主题也越来越明晰起来。观众中常有“官贵”出现,满脸堆笑手脚却严肃。这是一种修炼,一种精到。梅林戏在宋朝时, 专门到京都学习过宫廷舞蹈和其他娱乐文化,从那时它就开始抹去身上的土腥味,从那时它就慢慢把观众身份悄悄量身定位下来。醉眼的眯缝儿里,再品傩戏,那夸张的迈脚、舞胳膊扭脖子动作,像是当年斗我爹的“小将”们,那跳动的众神颤抖着肌肉,倒似努尔哈赤的子孙们又在摔跤……唉!当年那邹状元老人为什么要把这地方的土戏送到“皇宫老儿”那里去“洗脑净身”一番呢?结果是土掉不尽倒失了傩戏延续生命的功绩。王侯还不如一平民寡妇,前者虽说融进去的是皇家之气,但却把纯艺术往冷峻的工具领域里推去,而后者融进去的则是其他更土的乡戏的精华,使本土和外埠艺术彼此交相辉映,更裹紧了千万年丹霞的特有红色,使泰宁乡戏艺术永垂不朽!女人的奉献并不低于男人,而女人的功劳却又总是被掠夺,顶多划归于历史。
在尚书第欣赏这天下第一戏,倒是落得清静, 白炽灯始终是透明的,电子模拟的各种乐器声在暗红色的梁栋间和砖瓦缝里缠绕来去,碰撞得有声有色,最后夹带着古越遗风和集成电路焦灼之味混合一起再很有规律地滑进你耳朵,被土鸡土鸭和琴浪土酒抚摩过肠胃而后陶醉的观众们眯缝着眼儿,也跟着有节奏地一张一合着嘴和眼……真是爽!

戏台下失去忽明忽暗的光影,似乎也失去了乡土文化的精神,失去了乡民男女间特有的乐趣。倒是现代乡戏的导演们聪明,戏过半时来一场“相亲” 游戏,这种文明程度较高的“相亲”替代了乡民们在台下暗处的“不规矩”。移动着鹅步式的“媒婆” 引出八九位面带粉笑、裹着红红绿绿、染一身花草香气的妙龄女子游到身边,闹得人心里痒痒的,那眯着醉眼缝儿缩进木椅里似一团肉包子的男人们神志一下子被激活起来,快速地朝每位粉黛脸儿扫去, 随即本能地伸出手做拒绝状,被土酒浸抹过的手显得无力,只是挥去了刚才那自寻的孤独和专注,是意识中的某种严肃的警鸣突然受到了尊重,于是男人们又恢复了肉包状,稍有一两个胆大的,已把醉眼后面的某种东西藏进那些绝美的粉笑中。台下的女人们只有笑的份。
女人中是妻子的,在漫不经心的笑声中有意地把眼里的“制止”从斜视的缝角甩给缩在前椅里的丈夫,嘴里吐出的话倒也中听:去吧,挑位比我更好的!戏后,我问那位丈夫:老婆叫你当回“新郎” 你干吗不当?他回答道:你傻呵?老婆这叫火力侦察,以后会唠叨个没完!下次吧,我单独来……殊不知,那仅仅是笑一笑、说一说、闹一闹,那转眼即逝的乐趣在尚书第里你是带不走的,它归宅府里的李尚书统管,你只能把无尽的回味捎去,古今多少事不是都在笑谈中悄悄成为娱乐吗?但这种借助古越遗艺和青春魅力的娱乐,能使你跳脱出大城市喧闹的尘嚣,跃入洁净,心灵无垢。
演戏的人演戏,这是他们的职业;看戏的人看戏,这是他们的乐趣。这些,都是生存和生命的延续所必需的。我喜欢在乡下看戏的那种热闹劲儿, 也喜欢尚书第戏里戏外的鲜活,但我更欣赏从殷商先民中脱颖而出又走了三千多年的傩戏那难得的生命抗争力。领会乡戏之精妙,也就是在领会人世生活深层的达观与无穷的可能。
刊于《福建文学》2018年第7期
图片来自网络
TEX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