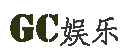鱿鱼游戏2深度解析:大逃杀类型作品的历史与人性试炼
路西法尔
参赛者被聚集到一个封闭的空间内,被迫展开生存游戏。游戏遵循一定的规则,被淘汰的人会丢掉性命,坚持到最后的人则能得到丰厚的奖励,背叛、阴谋还有残酷的人性试炼随之而来……

《鱿鱼游戏2》
早在2021年《鱿鱼游戏》爆红之前,「大逃杀」(Battle Royal)类型的小说、影视、动漫、游戏已经在较为小众的范围内流行开来。
实际上这个亚型最繁荣的时期是本世纪的前二十年:《大逃杀》(电影版2000)、《杀戮都市》(漫画版2000-2013)、《要听神明的话》(电影版2014)、《欺诈游戏》(漫画版2007-2015)、《弹丸论破》(游戏版2010)、《约定梦幻岛》(漫画版2016-2020)……
都是这个时期的作品,真正「出圈」的《鱿鱼游戏》赶上的是这一波流行的尾声,「圈里圈外」大概十五到二十年左右的「时差」。

《鱿鱼游戏》
和成熟的同类作品相比,《鱿鱼游戏》无论哪一点都算不上出彩:游戏设计其实相当草率,「忆童年」这个设定甚至有点儿戏,所有角色都是符号化的。黄东赫拍完第一集时压根没想到能火成Netflix访问量最大的剧集,也没有拍续集的打算。
如果说《鱿鱼游戏》比同类作品强在哪里,或许就是更加直白地点明了形形色色的「大逃杀」故事背后的「阶级」的隐喻:李政宰扮演的主人公是一个失业的工人,欠下巨额债务,一路上他战胜了流氓无产者(许承泰)、白领精英(朴海秀)并得到了脱北的女扒手(郑浩妍)的帮助,最后揭穿了巨富(吴永洙)的阴谋,而代表国家力量的警察(魏化儁)在这个过程中根本派不上用场。

《鱿鱼游戏》
就是这样一个工人阶级单挑巨富寡头的直白逆袭故事:有民族主义,有政治讽刺,但这些都是点缀,核心还是在阶级。本质上《鱿鱼游戏》就是男版的《灰姑娘》,更血腥、更刺激、更曲折而已。
本质上《鱿鱼游戏》就是男版的《灰姑娘》,更曲折而已。
所有的《灰姑娘》就不应该拍续集,灰姑娘成为了公主,丑小鸭化为了白天鹅,理当「永远地幸福下去」。
但迪士尼真的为《灰姑娘》拍了两部续集,黄东赫也改口拍出了《鱿鱼游戏2》。
他的理由也很直白:「尽管《鱿鱼游戏》第一季在全球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我并没有赚到什么钱。我必须要再拍第二季,才能补偿我第一季的成功所损失的报酬。」

《鱿鱼游戏2》
尽管数据显示《鱿鱼游戏2》仍然是当下Netflix最热门的剧集,但是无论热度还是口碑,第二季都比第一季下滑了不少。观众普遍反映这一季浪费太多时间在玩家投票和起义上了,脱离重点、节奏拖沓。
其实从这一季的第一集起,缝合游戏与现实的补丁就出了问题,黄东赫大费周章地铺垫李政宰如何寻找孔刘,而帮他找人的黑社会老大却煞有介事地说「这些年来欠了我钱的人几乎都毫无痕迹的消失了……」那他还找孔刘做什么,跟着欠钱的人不就完了?按这个思路,李政宰甚至可以干脆培养几十上百个卧底,全塞到小岛上去,还用得着自己以身犯险?
除了这种比较低级的编剧漏洞,第二季更显著的变化则是情感基调的变化。如果说第一季可以靠直白的阶级寓言和感官刺激给初次接触这一类型的观众带来震惊体验,在第二季试图完善世界观的时候,主创就无法延续这个简单粗暴的矛盾。
因为他必须解释:既然罪魁已经在第一季里死了,游戏为什么还能继续下去。

于是观众们看到,游戏不再是一种强加于玩家身上的压迫,而是被看作某种扭曲的福利制度。主办者从这一季的第一集起就强调玩家们是自愿的,甚至「善意」地设立了退出机制,被批评为冗长的投票情节机制上其实非常民主。
不论这样设计的初衷是否是政治讽刺,其结果就是责任被部分地推给了玩家,如果说第一季要传达的是「权贵实在太坏了,竟然拿穷人的命取乐」,第二季所传达的就是「这事穷人自己也有一点点责任。」直白的阶级批判让位给了老套的人性说教,自然就无法像第一季那样「爽」起来。

其实这也是「大逃杀」类作品的通病。拿这类作品的开山作:深作欣二的《大逃杀》来说,续集《大逃杀2镇魂歌》的口碑也远远不如第一部,像《约定梦幻岛》、《杀戮都市》这类长期连载则大多以虎头蛇尾收场。
归根结底,「大逃杀」传递的是现代人噩梦般的恶性竞争体验,容易理解却不容易找到一个明确的答案。生存游戏的尽头是又一场游戏,除非整个社会的形态发生改变,否则没有办法从游戏中彻底脱离;而且将模糊的梦境落实到现实当中则一定会出现圆凿方枘的情况,观众会觉得假。
这就是为什么「大逃杀」类故事一旦扩展世界观就容易烂尾的原因。

因此黄东赫在《鱿鱼游戏2》中乞灵于近似于极右翼的「深层国家」(Deep State)的阴谋论叙事几乎可以算是一种必然的选择。
主办鱿鱼游戏的权贵相当于暗中操纵一切的「深层国家」,玩家投票相当于对宰制自己的权力的认同,与极右翼对于民主选举结果的话术如出一辙,第二集中游戏策划者给李政宰讲的那个「红药丸」、「蓝药丸」的比喻被广泛地用于仇恨政治中的网络迷因中,李政宰的台词相当于吃下「红药丸」的觉醒者对于「深层国家」的宣言。

简单回顾一下上一季《鱿鱼游戏》爆火的背景就会发现从一零年代下半页开始,全世界媒体都在谈论西方工人阶级的「失落」:黄马甲、铁锈带、脱欧、特朗普……《鱿鱼游戏》的第一季能够爆红也是戳中了当时的社会情绪。
《鱿鱼游戏2》却碰触到了这套简单粗暴世界观的边界:为什么游戏主办人死了,游戏却还没结束?为什么灰姑娘已经变成了公主,却还要回来继续参加游戏?
一方面「深层国家」无所不能,它能掩盖真相、控制一切,一方面它又满是漏洞,可以凭借个体的觉醒获得救赎。这套叙事要想继续下去就必须营建起一套更深的「深层国家」来覆盖原来的阴谋论。

更为讽刺的是《鱿鱼游戏2》上映之前,Netflix在全球大张旗鼓的宣传活动。标志性的「英熙娃娃」伫立在全球的标志性场所,蒙面人纷纷「闯入」公共空间,打造起现实与虚幻交融为一体的超现实空间。
然而投资方用来做宣传的形象并不是身为反抗者的主人公,而是身为压迫者的主办方,公众则对此付之一笑,视之为一场嘉年华,可见无论戏里还是戏外,「革命」的基础并不存在。

如果说《鱿鱼游戏》是一面人性的镜子,那么它照出的与其说是人性的贪婪、险恶等阴暗面,不如说是映照出了再普通不过的自恋情结。
权贵们戴着面具,鬼鬼祟祟地凑到一个小岛上,看着穷人一边做儿童游戏一边被打得脑袋开花,到底有什么观赏性了?
这种不亚于皇帝老儿拿金锄头种地的想象能够唤起广泛的共鸣,只能从集体无意识的角度去思考。
李政宰和孔刘玩俄罗斯轮盘赌的时候,李政宰逼孔刘承认自己不过是一条权贵的走狗,言外之意是孔刘在人格上并不比玩家高人一等,应当承认对方的平等地位,结果孔刘宁肯给自己来一枪也不松口。

这段剧情里的两个人都很奇怪,完全没有来由地斗狠。其实情节也已经证明了整剧真正想要说什么:赢家和输家只是运气的区别,无关能力、无关德行,就是纯粹的运气。
李政宰玩这么大,不过是想代表广大输家向赢家讨一句认可。
三年磨一剑就磨出来这个?仆街活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