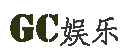索多玛的120天与鱿鱼游戏: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反思与对比
(2021年10月28日)
将皮埃尔·保罗·帕索里尼的电影《索多玛的120天》(1975)与黄东赫导演的《鱿鱼游戏》相提并论看上去有些奇怪,但我相信,帕索里尼所描绘的社会愿景与黄东赫在《鱿鱼游戏》中试图展现的目标很接近。
《索多玛的120天》改编自萨德侯爵1785年的小说。在电影中,帕索里尼试图将萨德侯爵的部分思想转化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反思:晚期资本主义的统治与奴隶制社会并无不同,自由和个人价值的承诺不过是个幌子。

《鱿鱼游戏》
《鱿鱼游戏》是Netflix迄今为止最受欢迎的剧集。
今年9月发布的第一个月内,它的浏览量就达到了1.11亿次。这部电视剧的灵感来自深作欣二导演的《大逃杀》(2000),而最为观众所熟知的,这类以生存游戏为蓝本的电影恐怕就是《饥饿游戏》三部曲了。

《饥饿游戏》
许多评论家都断言,《鱿鱼游戏》是对21世纪大多数人熟知的生活模式的一种转喻。Netflix这家面向大众的虚拟娱乐综合体能创造出让观众保留一个月记忆的作品吗?我们应该将《鱿鱼游戏》视为一部严肃的作品,还是将它看作是基于算法得出的大众畅销品?
另外一些人则坚信,《鱿鱼游戏》是对我们当下反乌托邦现实的记录——不是想象中的未来,而是资本主义体系下人们真实的生活状况。这个体系对自己的霸权是如此自信,以至于不厌其烦地将残酷的面孔藏在面具的背后。

作家弗朗斯西卡·牛顿在《雅各宾》杂志的署名文章中写道:「剧集中的整个游戏可能是个秘密,但是外部世界的暴行却并非如此。」就像我们渴望自己对某些富有批判力和洞察力的事物全神贯注一样,《鱿鱼游戏》是对我们当代社会和经济困境一份粗糙的记录文件。
让人感到惊奇的是,在第一集《一二三,木头人》中,来自巴基斯坦的阿里抓住了成奇勋的衣领,得以让他在命悬一线时逃脱机器人娃娃的捕捉。我们可以说,这种让角色们在残酷的环境下相互残杀,选出优胜者的制度,从根本上说是不人道、无情且病态的。

但是有趣的是,《鱿鱼游戏》并没有激起在现实中人们对贬低自身价值的那些「受害者」的愤怒。它是否真的可以帮助我们认清一些事,还是只是一个赚钱的剧集?
话说回来,影视业本就是一个赚钱的行业,《鱿鱼游戏》的估值为9亿美元。就内容而言,全世界成千上万的人加入了「鱿鱼游戏」的挑战,他们兴奋地把剧集的画面做成表情包,或者拍下一些搞笑的模仿视频上传到Tik-Tok上,看上去很有意思,不是吗?

作为一个寓言,《鱿鱼游戏》的价值如何?主人公是一个蓬头垢面的社会边缘人,他无法拯救自己的生命(想想游戏的剧情,这真是一个讽刺的双关语)。
在第一集中,我们看到他几年前被工厂解雇了,和年迈生病的母亲相依为命。至于剧集里的其他角色,他们大多是烦人、呆板、可疑、粗俗的,纯粹是穷人新自由主义想象的化身。
「鱿鱼游戏」参赛者的命运和奖金紧密相连,因为每当一个人死掉,小猪存钱罐里的奖金就越来越多。这是一个痛苦而深刻的寓言:人的生命已沦为了可量化、代替的价值。正如里尔克所言:只要有生命,同时就有死亡,生与死本质上是一体的。

「鱿鱼游戏」的参赛者是由001号「选手」(他解释说自己匿名参加游戏是因为参与比旁观更有趣)手下的一个神秘团队精心挑选的。这些富可敌国的精英阶层来说,手中的财富让他们变得麻木不仁。
《鱿鱼游戏》描绘了一帮无聊的自由主义者,他们像神一样,利用自己的金钱为所欲为。那些生活在持续的经济压力下,丧失了自己的尊严的穷人以及外来劳工,那些被讨债者跟踪和威胁的人,那些只是为了熬到周末而去借钱的人有弱点吗?这就是社会现实。也许你不能因为某人没有做过的事而斥责他们,但似乎那些没有出现在《鱿鱼游戏》中的事物才是重要的。

《鱿鱼游戏》是一部建立在人物行动,而非充分的社会调查之上的剧集。黄东赫省略了解释,将观众的注意力吸引到了别处。比如,在第八集《代表人物》中,可怜的女孩姜晓被尚佑残忍地割开了喉咙,像一只无辜的麻雀死在了自己的床上。
在其他部分,参赛者都在彼此残杀,要么杀害他人的妻子,要么杀死自己最好的朋友。在导演试图唤起观众共鸣的过程中,摄影机仍然采取了一种粗俗的呈现方式。剧集不断重复记录下子弹击中头部,或者血浆从脑中溢出的升格画面,然后接上幸存者恐惧、痛苦的表情。这些固定的表达和消费主义的图像在人的层面上,失去了怜悯心和感染力。

观众沉迷于《鱿鱼游戏》,但不会被触动。而且观众开始期待更多地看到这些画面,粗俗的暴力变得可以预测,导演沉迷于这种表达。结果真的非常无聊,以至于整部剧都变得很无趣,徒有其表:昂贵而精致的布景、特效以及每集240万美元的制作成本。
「鱿鱼游戏」在一个偏远的小岛上举行,这十分贴合萨德小说中呈现的特色,这些小说常以与世隔绝的城堡、阴郁神秘的森林或者暗无天日的地窖为背景——它们暗示着上帝、法律和道德的缺席,在这些地方,灭绝人性的游戏再也不必考虑社会的规则,再也不必承认生命个体的独立性。

在撒旦的地狱里,没有什么能强迫另一个人为了保护他人而牺牲自己的幸福。在这样的制度下,那些人类善良的品质,例如爱、善心、宽容和正义却让一个人变成受害者,在《鱿鱼游戏》中,他们是那些死去的人。
诚然,萨德笔下的那些自由的性放荡者和其他任何人一样,都会因为判断失误而受到无情的惩罚。黄东赫说得对:让情绪支配人们的行为是最愚蠢的错误。
这些可怜的角色之所以被招募到「鱿鱼游戏」中,是因为他们正处于不公正、不安的境地。为了一条出路、一线生机、一个更好的生活机会,他们会不惜一切代价。换句话说,他们想用一个机会来调转一切。「你听好了,」成奇勋说,「我不是一匹马,我是一个人。」

黄东赫并没有做太多的社会调查。如果他做了,他也许能够发现存在的残酷性的理由;在没有社会调查的情况下,他似乎没有过多的发言权。韩国经济不平等的真实原因是什么?债务危机提供了一个直白的解释——为何有那么多人愿意并留在那个反对社会大多数的地狱里。
人们可能会注意到,冒着被称为真正的道德恐慌传播者的风险,《鱿鱼游戏》的宿命论和犬儒主义是危险的,这部剧集看上去是一部时代文献,也许它的价值也仅限于播出的这段时间,却没有记录性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