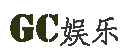阿摩司·奥兹故事开始了:探索小说开头的奥秘与作者读者的契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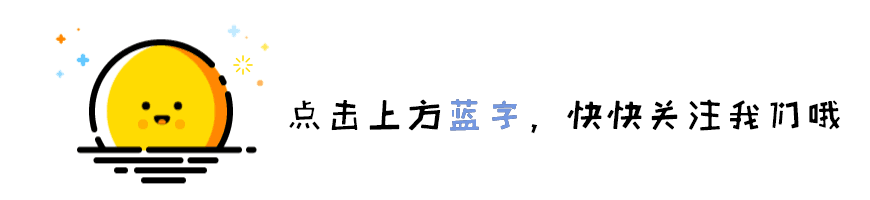
在阿摩司·奥兹看来,故事的开头是应该细读的,它是作者和读者之间的契约。于是,他在《故事开始了》一书中精选了十部小说,果戈理、卡夫卡、契诃夫、卡佛、马尔克斯……如何阅读他们故事的开头,如何辨析开头和通篇的联系。作者怎样兑现他和读者之间的约定,这些问题的探究,在奥兹的条分缕析下像游戏般有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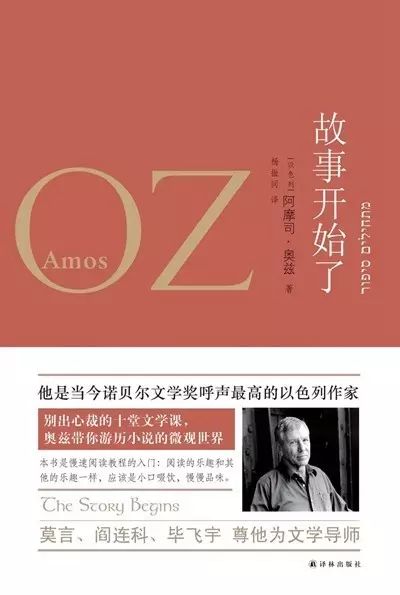
《故事开始了》,[以色列]阿摩司·奥兹著,杨振同译,译林出版社2013年1月
一些犀利(尖酸刻薄)的文学学者如特里·伊格尔顿之流,甚至能从小说开头的分析中解读出作者心里的各种小九九,真是“杀人”还要“诛心”。不可讳言,好的开头是成功的一半,好比DNA隐藏着生命体全部的遗传密码,它将奠定全书的行文基调、叙事方式和语感,甚至一句话能开出一个门派。例如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最为有名的第一句:
许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将会回想起,他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
这句话几乎影响了所有的先锋作家,我们会在莫言、余华、马原、格非、孙甘露的作品中读到其各种版本的变体。如果在所有的小说开头中评选出“影响因子”最高的一句,那么马尔克斯这句一定能名列前茅。
这位上校同志真是个直男,都面对行刑队了,脑子里想的竟然不是罗曼史或热恋的情人,而是冷冰冰的冰块。大概《百年孤独》的读者,宅男偏多,与书名正好相得益彰,活该孤独百年。女性读者也许更喜欢法国风格的,无论从译文的美感度来说,还是从场景的吸引力来说:
我已经老了。有一天,在一处公共场所的大厅里,有一个男人向我走来。他主动介绍自己,他对我说:“我认识你,永远记得你。那时候,你还很年轻,人人都说你美,现在,我是特为来告诉你,对我来说,我觉得现在你比年轻的时候更美,那时你是年轻女人,与你那时的面貌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面容。”
试问哪个女人不害怕美丽容颜的消褪,所以,又有哪个女人经受得住这样的甜言蜜语?叶芝的一首《当你老了》,为这位写过许多晦涩诗歌的大诗人赢得了许多“脑残粉”,以至于叶芝在不少姑娘的心目中与徐志摩相去无几。我相信,不需要王小波的推崇,玛格丽特·杜拉斯靠着《情人》的开头,就足以吸引大量读者购买——用于写情书的参考。
爱情的确是文学发展的第一推动力,遥想古希腊时代,为了追求海伦而引起的争端,诞生了荷马史诗的创作素材。所以在小说的开头谈情说爱、谈婚论嫁,实在是招徕观众的方便法门:
洛丽塔,我的生命之光,我的欲念之火。我的罪恶,我的灵魂。洛——丽——塔;舌尖向上,分三步,从上颚往下轻轻落在牙齿上:洛——丽——塔。(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洛丽塔》)
凡是有钱的单身汉,总想娶位太太,这已经成了一条举世公认的真理。(简·奥斯汀《傲慢与偏见》)
甚至连伟大的托翁都未能免俗,《安娜·卡列尼娜》的开头,不是以最初拟定的“奥布隆斯基家里一切都混乱了”这一颇具史诗般雄浑高雅的句子开始,而是编造了一个脍炙人口然而纯属偏见的关于婚姻与家庭的“金句”: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所有跟配偶吵架的文青,都能背出这句托翁名言。托翁真是深谙人心,在对叙事艺术处女座般的追求中也不忘给读者制造一些QQ签名的好段子。
当然,也有不考虑读者的装逼作者,例如麦尔维尔《白鲸》的开头:
“管我叫以实玛利吧。”
第一句就得加一条长长的注释,取个名字还暗藏《圣经》典故,欺负我们没读过书?相比之下,查尔斯·狄更斯的装逼,就显得可爱多了,尽管此君的形式逻辑课一定考不及格:
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代,这是怀疑的时代;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绝望之冬;我们应有尽有,我们一无所有;我们一起走向天堂,我们一起走向地狱。(《双城记》)
20世纪现代主义文学的开头,因为作者对小说艺术的刻意求工,就更有象征意味了。然而有时放在一起对比,却往往造成离奇的喜剧效果。例如同样是睡觉,普鲁斯特在《追忆似水年华》开篇一展法国贵族式的慵懒和优雅:
在很长一段时期里,我都是早早就躺下了。
然而紧张的卡夫卡考虑的却是:
一天早晨,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变形记》)
简直让人没法安心睡觉!
同样是介绍主人公,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老老实实从“我来到这个世上”开始,主人公虽然命途多舛但毕竟还是个正常人,然而20世纪的小说,主人公们就是不好好说话:如果说“我是一个看不见的人。”(拉尔夫·艾里森《看不见的人》)是神话,那么“我是一个死人。”(奥尔罕·帕慕克《我的名字叫红》)就是鬼话了。至于“现在在哪里?现在什么时候?现在是谁?”(萨缪尔·贝克特《无名者》),简直就是酒鬼喝醉后的胡话。
真正有头脑的,还得算是马克·吐温和卡尔维诺,他们竟然在开篇这一书籍的黄金位置给自己的书打起了广告:
你要是没有看过一本叫做《汤姆·索亚历险记》的书,你就不会知道我这个人。不过这没有什么。那本书是马克·吐温先生写的……(《哈克贝利·芬历险记》)
你即将开始阅读伊塔洛·卡尔维诺的新小说《寒冬夜行人》了。(《寒冬夜行人》)
同样是先锋作家,为什么卡尔维诺的书就能卖得这么好,市场经济的先进经验,值得我们学习!
言归正传,中国的当代作家,小说开头写得精彩的,不乏其人。中国人好面子,小说的结构和结尾就算编织得不高明,这“第一炮”的开门红却是一定要打响的,美其名曰——“凤头”,所谓:“开卷之初,当以奇句夺目,使之一见而惊,不敢弃去,此一法也。”小说的第一句叙事,通常蕴含着该小说的全部叙事信息。这里列举数位茅盾文学奖得主的小说开头,看看都有哪些一见而惊的“奇句”。庶几管中窥豹。
开头
陈忠实(第四届茅盾文学奖)
白嘉轩后来引以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
难以想象,一部宏大的“史诗”竟然是这样开头的。英雄们还未展示其高大的形象,镜头就对准了他的下半身。如果是伪君子,只怕就要遮遮掩掩,恼羞成怒。然而被读者大窥房事的“英雄”白嘉轩,却并不因此而减色。这就是陈忠实的独到之处,也是《白鹿原》无法超越的地方:能让读者带着读小黄文的心情,邂逅一部伟大的作品(外国文学中能与之媲美的只有纳博科夫的《洛丽塔》)。陈老行文的气魄,从第一句贯穿到小说的最后一句,中间没有一刻是软下去的,确确实实可以“引以豪壮”。

《白鹿原》,陈忠实著,长江文艺出版社2014年7月
开头
阿来(第五届茅盾文学奖)
那是个下雪的早晨,我躺在床上,听见一群野画眉在窗子外边声声叫唤。
母亲正在铜盆中洗手,她把一双白净修长的手浸泡在温暖的牛奶里,嘘嘘地喘着气,好像使双手漂亮是件十分累人的事情。她用手指叩叩铜盆边沿,随着一声响亮,盆中的牛奶上荡起细密的波纹,鼓荡起嗡嗡的回音在屋子里飞翔。
如果说《白鹿原》的开篇是男子汉的豪壮,那么《尘埃落定》的开篇简直就是荣国府中宝二爷的自白了。《红楼梦》里的宝二爷“有些呆气”,《尘埃落定》里的二少爷就是个“傻子”,开篇写这位13岁的傻子起床时的所见所思,空灵跳跃,自由洒脱,行文神采飞扬。仅从小说开头就不难看出,阿来是在与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的第一章一较短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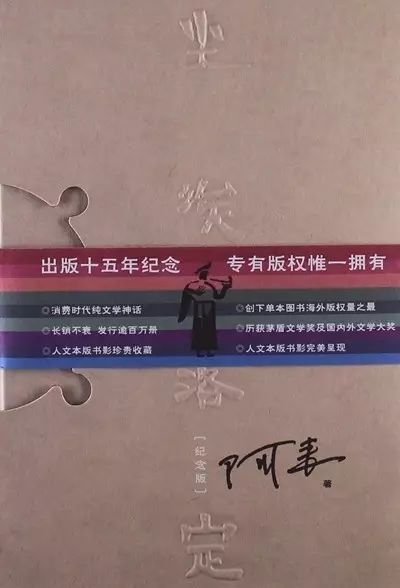
《尘埃落定》,阿来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4月
开头
王安忆(第五届茅盾文学奖)
站一个至高点看上海,上海的弄堂是壮观的景象。它是这城市背景一样的东西。街道和楼房凸现在它之上,是一些点和线,而它则是中国画中称为皴法的那类笔触,是将空白填满的。当天黑下来,灯亮起来的时分,这些点和线都是有光的,在那光后面,大片大片的暗,便是上海的弄堂了。那暗看上去几乎是波涛汹涌,几乎要将那几点几线的光推着走似的。它是有体积的,而点和线却是浮在面上的,是为划分这个体积而存在的,是文章里标点一类的东西,断行断句的。那暗是像深渊一样,扔一座山下去,也悄无声息地沉了底。那暗里还像是藏着许多礁石,一不小心就会翻了船的。上海的几点几线的光,全是叫那暗托住的,一托便是几十年。这东方巴黎的璀璨,是以那暗作底铺陈开。一铺便是几十年。如今,什么都好像旧了似的,一点一点露出了真迹。
我相信,站在一个至高点看垃圾场,也会是壮观的景象。距离能够产生美感,模糊掉一切肉眼能见的肮脏。王安忆《长恨歌》里的行文,和她的女主人公王琦瑶一样,绝对是风情万种的,然而也是面貌模糊的,例如这段点啊线啊光呀暗呀的,完全看不出是弄堂,倒像是在看“几何原本”了。王安忆对上海的市民气息是相当熟悉的,然而,是不接受的。所以她只能选择站在一个至高点来看这座城市,以让自己“眼不见为净”。正如作者自己所说:“面对上海这么一个写作材料,我是有些遗憾的……上海这座城市历史太短,物质太多,人也因此变得不够浪漫。”而这,恰恰就是小说开头巧妙透露给读者的信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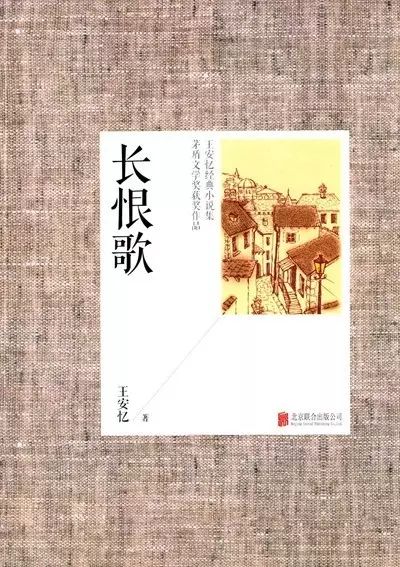
《长恨歌》,王安忆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年11月
开头
贾平凹(第七届茅盾文学奖)
要我说,我最喜欢的女人还是白雪。
喜欢白雪的男人在清风街很多,都是些狼,眼珠子发绿,我就一直在暗中监视着。谁一旦给白雪送了发卡,一个梨子,说太多的奉承,或者背过了白雪又说她的不是,我就会用刀子割掉他家柿树上的一圈儿皮,让树慢慢枯死。这些白雪都不知道。
如果说《尘埃落定》的叙事是“傻子说梦”,《秦腔》的叙事则是“疯子胡吣”了。胡吣自然是家长里短、鸡毛蒜皮。然而贾平凹的本事,就是从家长里短、鸡毛蒜皮中写出人生的生死悲欢,社会的动荡兴衰。疯子的话语是对生活无意义的隐喻——一场被阉割的疯狂爱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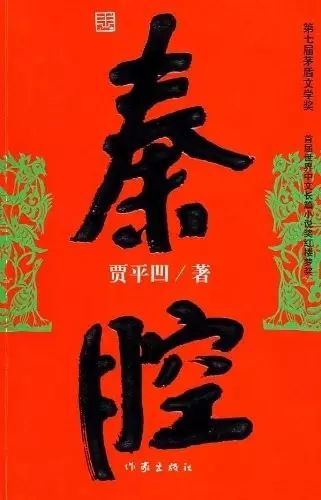
《秦腔》,贾平凹著,首发于《收获》2005-1、2期,作家出版社2005年4月
开头
莫言(第八届茅盾文学奖)
马洛亚牧师提着一只黑色的瓦罐上了教堂后边的大街,一眼便看到,铁匠上官福禄的妻子上官吕氏弯着腰,手执一把扫炕笤帚,正在大街上扫土。他的心急剧地跳起来,嘴唇哆嗦着,低语道:“上帝,万能的主,上帝……”他用僵硬的手指在胸前画了个“十”字,便慢慢地退到墙角,默默地观察着高大肥胖的上官吕氏。她悄悄地、专注地把被夜露潮湿了的浮土扫起来,并仔细地把浮土中的杂物拣出扔掉。
尽管莫言是以小说《蛙》获得茅盾文学奖,但正如余华所说:“从文学的标准来看,莫言起码可以拿10次茅盾文学奖。”我最喜欢的是《丰乳肥臀》的开篇,语感颇有《尤利西斯》开篇的味道。然而一转眼,又是母驴难产,又是婴儿接生,又是鬼子进村,杂乱中洋溢着顽强的生命力,画面变得立体起来。能用线性的文字叙述出3D电影的感觉,现代文学有端木蕻良,当代作家则是莫言。
《檀香刑》,则宛然《百年孤独》的中文版本,只是远比《百年孤独》啰嗦,没办法,谁让叙事者假借的是饶舌的“狗肉西施孙媚娘”,这也算是艺术真实吧:
那天早晨,俺公爹赵甲做梦也想不到再过七天他就要死在俺的手里;死得胜过一条忠于职守的老狗。俺也想不到,一个女流之辈俺竟然能够手持利刃杀了自己的公爹。俺更想不到,这个半年前仿佛从天而降的公爹,竟然真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

《莫言长篇小说全编》,莫言著,浙江文艺出版社2017年1月
莫言长篇《蛙》首发于2009年第6期《收获》
开头
格非(第九届茅盾文学奖)
一九五六年四月的一天,梅城县县长谭功达乘坐一辆吉普车,行驶在通往普济水库的煤屑公路上。道路的左侧是一条湍急的河流,岸边长着茂密的苇丛和菖蒲,成群的鹭鸶掠水而飞;在公路的右侧,大片的麦田和棉花地像织锦一样铺向远处的地平线。一畦畦的芜菁、蚕豆和紫云英点缀其间,开着白色、紫色和幽蓝的花。
谭功达神情阴郁,心事重重。他的膝盖上摊着一张破烂不堪的地图,那是一张手绘的梅城县区域行政规划图。他不时地用一枝红铅笔在地图上圈圈点点。地图下面,秘书姚佩佩的小腿随着汽车的颠簸,有节奏地磕碰着他的神经。他不由得抬起头来看了她一眼。姚佩佩穿着一身咔叽布列宁装,原先的蓝色布料早已退了色。梳着羊角辫,长长的脖子上有一条深红色的围巾。她正和坐在前排的副县长白庭禹说着什么。她吃吃地笑着,柔软的腰肢扭来扭去,还不时朝窗外指指点点。
“怎么会有那么多的仙鹤?它们往那里飞?”姚佩佩问道。
“傻孩子,那可不是什么仙鹤!那是鹭鸶和江鸥。”白庭禹纠正道。
“那是什么?怎么还在动?”姚佩佩趴在白庭禹的肩头,伸手朝远处指了指。
“噢,那是长江中的帆船。船身让高高的江堤挡住了,你只能看见帆尖在走。”(《山河入梦》)
格非不但在小说的叙事语感上出类拔萃,而且也是中国作家群中少有的学者型小说家。学者格非,并不是在小说中以炫博学,而是往往玩一些“无一字无来历”的文字戏仿。例如“江南三部曲”中第二部《山河如梦》的开头,就很难不让人想起卡尔维诺的《一个分成两半的子爵》:
我们和土耳其人打过一场仗。我的叔叔,就是泰拉尔巴的子爵梅达尔多,在波希米亚平原上骑着马直奔基督教徒宿地。一个叫库尔乔的随从跟着他。一大群白鹳在浑浊、停滞的空气中低低地飞过。
“怎么会有这么多白鹳?”梅达尔多问库尔乔。“它们飞到哪儿去呢?”
……
“它们往战场飞,”随从神情阴郁地说。“它们要一路陪着我们呢。”
这绝不能视作“抄袭”,因为以格非的知识水平和叙事能力,完全可以避开“英雄所见略同”的“尴尬”。我相信这是他故意的,正如有评论家指出,格非笔下的“中国经验”与西方现代后现代经典文本有着显豁的“互文”关系。格非在这种互文关系中乐此不疲,在小说的开头戏仿一下卡尔维诺或博尔赫斯,正是这位先锋小说家的应有之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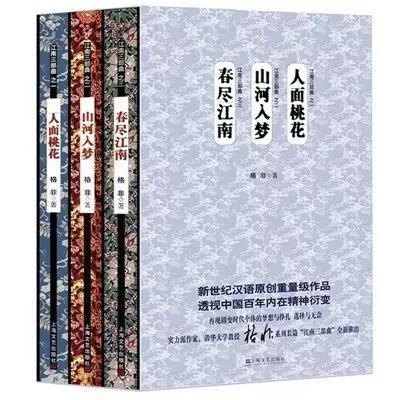
《江南三部曲》,格非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1月
附:余华
1965年的时候,一个孩子开始了对黑夜不可名状的恐惧。我回想起了那个细雨飘扬的夜晚,当时我已经睡了,我是那么的小巧,就像玩具似的被放在床上。屋檐滴水所显示的,是寂静的存在,我的逐渐入睡,是对雨中水滴的逐渐遗忘。应该是在这时候,在我安全而又平静地进入睡眠时,仿佛呈现了一条幽静的道路,树木和草丛依次闪开。一个女人哭泣般的呼喊声从远处传来,嘶哑的声音在当初寂静无比的黑夜里突然响起,使我此刻回想中的童年颤抖不已。
在众多当代实力作家中,余华算是茅盾文学奖的最大遗珠。因题目所限,此处以附录放上我最为击节赞赏的《在细雨中呼喊》的开头,尤其“使我此刻回想中的童年颤抖不已”,实在是神来之笔。无怪乎众多读者对余华如今的作品表示失望,有此珠玉在前,即便后出之作写得不差,也只能是“曾经沧海难为水”了。

《在细雨中呼喊》,首发于1991-6《收获》,余华著,作家出版社2012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