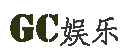王家卫“不响”,胡歌马伊琍陈龙对谈“繁花”
改编自金宇澄的文学母本,王家卫的电视剧《繁花》,一拍就是三年。
胡歌说,它补足了记忆中的那一块拼图。
马伊琍记得,有一场戏拍了36条,也可能是46条。
陈龙在杀青那天,凌晨两三点回到家中,在写字台上写下“我就是陶陶,他不会离开我”。
这是《繁花》烙印在演员身上的印记。12月30日晚间,演员们齐聚上海图书馆东馆,与读者们共度“《繁花》之夜”,现场不出所料座无虚席。在讲座开始之前,他们接受沪上媒体采访,聊起这部剧之于自己的意义。
“仿佛看到了我的父亲”
在金宇澄的原著小说《繁花》中,有1000多处“不响”。2020年9月10日,胡歌印象深刻的开机第一天,他从导演王家卫那里得到的答案也是“不响”。那天拍的场景是雪芝的家,即将拆迁了,阿宝故地重游。胡歌发现一件奇怪的事,空屋里没有雪芝的照片。“剧里没有沪生、小毛,雪芝或许是阿宝和过去产生关系的唯一途径。”出于好奇,他发消息问导演,戏里到底有没有雪芝?“等了很久,导演回了两个字:不响。”
演员胡歌,张熠摄
在胡歌看来,《繁花》补足了自己记忆中关于1990年代的那一块拼图。“我的父母和沪生、小毛一样,共同经历了那个时代。对于他们的经历,我充满好奇,也从只言片语中了解到当时他们经历的人和事,但始终没有一块完整的拼图。很多时候再多问一些,他们就跟小说一样,不响。”于是,当《繁花》这本小说出现时,他如饥似渴地阅读,借此完成对那个时代认知的拼图。“可能在见到王导之前,我生活的很多部分就在《繁花》的世界里。”
在胡歌的记忆里,90年代的人都很忙,包括父亲及他身边的朋友,大家都嚷着要去做生意。隔三岔五就会有人到家里来,“谈的似乎都是大生意,但也没看父亲赚到钱,好在也没亏钱。小孩子对那个时代的认知是很肤浅的。那个时代,每个人都相当亢奋。《繁花》影像中所传达的、表现的上海,都和那个时代的人的精神状态是吻合的。”
《繁花》剧照
就是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中,阿宝摇身一变成为宝总。“宝总这个人物有时代的复杂性和撕裂感。不管宝总在事业上做得如何风生水起,他心里永远是有一个阿宝的。”胡歌开了个玩笑,头发梳上去就是宝总,梳下来就是阿宝。宝总和平饭店的包间里,永远摆着一缸金鱼。这是导演埋下的伏笔。“看过书的读者和观众,马上就能感受到金鱼代表着什么。希望在接下去的22集里,大家能去寻找导演为阿宝埋下的伏笔。”
拍完戏看回放时,王家卫有个习惯,他会打开音乐,带着BGM一起看。胡歌依稀记得是《美国往事》里的音乐。“母亲离开后,我和父亲独处,他年纪大了,会说起以前的故事。拍戏过程中,我发现越来越理解我的父亲。在监视器前看回放,我仿佛看到了我的父亲。”
“演得不好给你剪掉”
在很多场合,胡歌都用“孙悟空与猪八戒”的关系形容剧中玲子和宝总的关系。当然,马伊琍饰演的玲子是孙悟空,宝总才是猪八戒。“这是玩笑的说法,在阿宝到宝总的转变过程中,玲子一直在帮他。夜东京就是避风的港湾,阿宝在黄河路上叱咤风云,到了夜东京,每次都会被玲子教育。昂首挺胸进去,灰头土脸出来。”胡歌说。
对于玲子这个角色,马伊琍觉得她是典型的“刀子嘴、豆腐心”。“玲子身上有上海女性非常闪光的一面。在阿宝周围的女性角色中,玲子身上母性的色彩更多一些。她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女性。上海人比较在意体面,呈现在距离感、安全感等方面。玲子和阿宝之间有张有弛、你来我往,是有距离感的。她会配合阿宝的体面,阿宝也是如此,这部分是由地域的秩序感产生的。”
演员马伊琍,张熠摄
在王家卫的剧组拍戏,没有固定的剧本,演员们每天到了现场化妆的时候才会拿到剧本,每个人都不知道除自己之外的戏份、布局、人物走向。“你们看到的很多精彩表演,都是在半夜三四点完成的。”马伊琍说。
有一场戏,令她几乎感到受挫。“那次拍玲子看阿宝的镜头,拍了6条过了。王导突然说,想让我演一个‘看见他就像看见空气’的感觉。从11点拍到凌晨两点,没有喝一口水,也没有坐回凳子上,我穿着高跟鞋一直上上下下,不知道拍了多少条,一直无法拍到他满意。导演说,我的眼睛里他感觉不到那么空的东西。”那时候,马伊琍很沮丧,因为职业生涯中很少有这种让导演不满意的时刻。“王导就过来拍拍我肩膀,请场记过来,忘了是36条,还是46条。导演说,你这个条数,NG前十名都没进去,他们不都活得好好的吗?”这一晚收工后,马伊琍没睡好,复盘了整晚,发现可能是自己本能地在抗拒导演要求的第二种表演方式。“第二天,我重新换了一种表演方式,拍了五六条也就过了。”
《繁花》剧照
金宇澄也讲过一个故事。有一次他去探班,导演在拍阿宝的一个面部特写镜头。一次、两次、三次,拍到第42条时,已经是半夜两点。他忍不住插话,说可以了,可以结束了。结果,王家卫导演和胡歌同时回转头问,为什么?后来,金宇澄向上海文艺出版社副社长李伟长讲了这个故事;30日晚上,李伟长又在上图东馆,把这个故事讲给当天的观众听。
马伊琍笑言,在片场,王家卫有一句话——“演得不好给你剪掉”。为了不被剪掉,所有演员都拼尽了全力。“很难用语言去形容这三年的工作。唯一可以让大家去感受的是,你去看戏的时候,一定会看到我们脸上岁月的变迁。三年前的眼神是很懵懂的,一切都是未知的;三年后杀青的时候,其实眼神里是有疲惫的,我觉得这符合生命的一个过程。”
“我就是陶陶,他不会离开我”
出现在记者面前的陈龙,穿了一件高领毛衣,外搭格子复古服装,有点像是《繁花》里陶陶的装扮。“陶陶真的也有一件差不多的衣服。”为一部戏拍摄3年,杀青那天,他很难和“陶陶”这个角色告别。
演员陈龙,张熠摄
“3年,在我的拍摄生涯中是顶峰的时间。拍完最后一个镜头,我很失落,正因为时间长,会跟角色、剧组建立起这样的情感。”陈龙记得,当时是拍一场和胡歌的对手戏,导演拍拍肩膀,告诉他这是最后一个镜头。演完后,大家开始鼓掌,恭喜杀青。“那时候心里难受,就跟自己说,陶陶要离开我了。正好这一幕被导演听到了,他说放心吧,不会的,你就是陶陶。”那天,陈龙回到家已经凌晨两三点,他在写字台上把这句话记了下来——“我就是陶陶,他不会离开我”。
进《繁花》剧组之前,陈龙光试戏就试了4次,每次心情都像过山车,不知道到底导演用不用他。在他看来,电视剧中的陶陶,要比原著中的陶陶幸福,因为有他的底线。“导演对这个角色做了很大改编,剧中沪生和小毛都没出现,导演说在看原著陶陶的时候,也要了解小毛的人物性格,我觉得他是把这两个人物做了糅合。”陈龙说,《繁花》既不好拍,又很好拍,“你只要听导演的,你相信他就很好拍;说不好拍,是戏确实有难度。这三年,导演把我表演的部分不断去掉,要的是我在剧中生活,这是《繁花》这部戏最大的收获。”
跟宝总包间里的鱼缸一样,陶记海鲜档里也藏着许多细节。阿宝和陶陶的出身截然不同,两人如何成为赤裤兄弟,剧里并未着墨太多。但其实海鲜档的墙上贴着两人年轻时的照片,桌面的玻璃下也压着合影。包括90年代黄河路上最流行什么海鲜,剧组请了专人做指导。“这些道具、细节,可能特写不是很多,但对演员的代入感是特别强的。”
拍戏三年,演员们用沪语演完了整部《繁花》。电视剧播出后,马伊琍听到周围朋友笑话家里的“小洋泾浜”,看沪语版时还要看字幕,“方言是文化里非常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有一些话只能用俚语来表达,会说到你心坎里去”。陈龙觉得,拿上海话演戏其实就是在生活,“说沪语就是一种生活的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