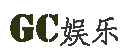日本恐怖片的文化焦虑表征:新浪潮与日式恐怖片的演变与社会变革
(2024年10月29日)
与其他任何类型相比,恐怖片都更像是文化焦虑的表征——仿佛你可以从人物的皮肤上看出这种紊乱,就像荨麻疹一样。在日本这个总是充满了对社会压力的狂野表达的国家,这种现象产生了两个主要的浪潮: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新浪潮冲击,以及80年代末和90年代的日式恐怖片来袭。虽然这些阶段反映了不同的社会变革,但从宏观上一起看来,它们就像一个萦绕不散的幽魂。
新浪潮恐怖片主要以日本封建社会初期到江户时代的广阔历史为背景。在美国,「旧西部」只适用于西部片,但在日本,中世纪一直是任何类型或模式的成熟时期。这两个时代都处于巨变之中,它们代表了从半开化的无政府状态到现代性的演变(尽管旧西部有着巨大的神话色彩,但从1803年路易斯安那购地开始,旧西部时期只延续了85年,而日本则有超过几百年的时间可以作为拍摄背景)。
历史始终是民间故事,包括「怪谈」(鬼故事)的发源地,而这正是新浪潮挖掘的宝藏;继沟口健二的《雨月物语》(1953)展现了氤氲缭绕的鬼魅气息之后,最著名的怪谈改编作品包括新藤兼人的《鬼婆》(1964)、《黑猫》(1968)和《铁轮》(1972);中川信夫的《怪谈连篇》(1957)、《鬼猫凶宅》(1958)和《东海道四谷怪谈》(1959);小林正树的《怪谈》(1964),以及安田公义和黒田義之的《妖怪三部曲》(1968-69)。就像由汉默电影公司引领的英国哥特式恐怖片的几乎同时期的创作高潮一样,五、六十年代的日本电影沉浸在鬼魂不散的非现代过去,既给人野性和原始的感觉,又似乎遥远得没有威胁。

《雨月物语》
但至少在新藤兼人看来,过去的一切都充满了威胁,他的标志性恐怖片充满了新浪潮式的愤怒和愤世嫉俗。《鬼婆》是新浪潮中出现的最可怕的作品之一,在战后的全国性运动中,新浪潮以其坦率的社会批判以及对折磨、性侵犯和堕落的迷恋而独树一帜。这个要追溯到封建时代的故事,源于15世纪僧人莲如的一则佛教民间传说,情节残酷无情:一个老妇和她的儿媳(儿子/丈夫被劫持,再也没有回来)在一大片野草丛生的平原上过着野人般的生活,她们通过跟踪和杀害路过的士兵来养活自己,把他们的盔甲和刀剑卖给当地的商人,然后把尸体扔进一口隐蔽的井里。
当第三个丛林掠夺者——一个和两位女人一样精明的逃亡士兵——闯入这个不稳定的关系网时,一切都乱套了,边疆生存的清晰度被汗水、性的非理性——在这个蛇窝里几乎是一种正常的人类冲动——以及从一个被谋杀的武士毁容的脸上摘下的被诅咒的般若面具所掺杂。当士兵走出商人的巢穴,与另一对晒得黝黑、活力四射、手里拿着掠夺来的武士战利品的婆媳搭档擦肩而过时,你不禁会问,新藤的悲观怎么会如此冷血。

《鬼婆》
无论是哪个国度拍摄的电影,都很少有一部能揭露出这样的毒性,即在强权即公理的父权制社会和既隐喻又邪恶的食人神秘景象中,被抛弃的女性变成了野兽。影片中完全是道德真空,对家庭和爱情的任何关怀早已烟消云散,只有丛林法则。鉴于沟口和小津始终坚持新生的女权主义,对日本女性苦难的叙事着迷并不罕见,但新藤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职业生涯中,对日本崇尚阳刚气概的社会中的性别虐待尤为愤慨。
在其他导演的作品中,可能没有这么多残酷的性对抗或性侵犯,而《黑猫》则是另一部从受折磨的女性视角描绘封建荒野的作品。在与《我唾弃你的坟墓》(1978)颇有些相似的一个场景中,封建时代的一对被轮奸婆媳化身为猫一般的吸血鬼,引诱并消灭了路过的一队队浪荡武士,直到一名年轻的武士受大将军之命去消灭在罗生门徘徊并喝下大量人血的怪物或怪人。令他懊恼不已的是,他最终意识到这两个来势汹汹的神秘生物正是自己的母亲和妻子。与《鬼婆》中的平原一样,这部电影里的竹林也被拍得如梦似幻,到处都是夜影和发光的雾气,即使我们身处鬼魂虚幻的房子里,有时通过巧妙的双重曝光,房子似乎也会在黑暗的森林中自行滑行。然而,狂热的类型特质很难让我们从最后的母子对决、肢体搏斗的悲剧性政治意图中走出来,这是一场自以为是的父权强权与无数愤怒、受虐的女性之间的对峙。

《黑猫》
这就是当时的社会境况。到了80年代,现代性本身开始变得令人不安。日本恐怖片的焦虑关注和表现政治随着转向「日式恐怖片」而发生了变化(在此之前,日本电影人曾进行过大量与恐怖相近的朋克实验,如大林宣彦于1977年拍摄的《鬼怪屋》和冢本晋也于1989年拍摄的《铁男1:金属兽》)。历史时机已经成熟,不确定性占据上风:1989年既是裕仁天皇看似无限统治的终结之年,也是日本巨大经济泡沫破灭之时,90年代的日本陷入了通货紧缩的漩涡。电影人开始抛弃传说中的过去,转而关注二十世纪末的焦虑,其中最突出和最有预见性的是数字技术的幽灵。
自60年代以来,日本一直在科技领域占据世界主导地位,他们最先看到这种新奇的现代性正在向我们袭来,而在电影领域,改变游戏规则的当然是中田秀夫的《午夜凶铃》(1998),这是一部简单而潜藏暗流的低俗电影,以一个空洞的都市传说为前提——一盘闹鬼的录像带,人们一旦打开观看,就会受到诅咒在七天内猝死。正是这种犯忌讳的视频蒙太奇让我们寝食难安:这大概正是你曾经所想象的死人凝固的愤怒,如果从以太中攫取并以数字信号的形式呈现出来,这一系列莫名其妙的影像是在没有摄影机的情况下产生的,支离破碎,残留着难以名状的恶意。画面甚至还没有切到树林中的那口井,最终有什么东西从井里爬了出来。在叙事上,影片的整个重点就是你不应该看到它,而中田却让我们看到了它——一举加剧了恐怖电影在最危险的时候所造成的心理情感创伤。(至于这些影像是如何出现在录像带上的,这仍然是一个悬而未解的问题——当然,日本人对将思想印刻在摄影材料上的这一现象也有一个专门的名称:「念写」[nensha])。这部电影与大卫·柯南伯格的《录影带谋杀案》(1983)一样,是一部让人在午夜时惊恐万分、对屏幕充满恐惧的电影,就像那盘被诅咒的录像带一样,是罗夏测验的墨迹,但每一次解读都可以追溯到我们自身的良知——我们是如何感知现实的——与技术入侵现实的方式之间存在着不可知的、甚至奇怪的超自然空隙,而技术似乎又在我们的理解之外发挥着作用。像幽灵一样。

《午夜凶铃》
《午夜凶铃》引发了续集、衍生作品和翻拍,但中田紧随其后推出了《鬼水怪谈》(2002),该片击中了另一个不同的当代骇人主题:在一个真实的鬼故事中,我们看到了气候变化的多米诺骨牌,尤其是,你的家和家人被无情的雨水、漏水、洪水和霉菌摧毁的感觉。影片将一场噩梦般的失控监护权争夺战,与每个房主对家庭世界被水淹没的恐惧,结合在一起——恼人的、不断转移的天花板污渍就像幽灵一样,是过去漏洞的残留物,具有威胁性且无法根除——影片将令人不安的洪水作为来世不平静的有效隐喻。只需微微一暗示,你就会想到我们正在加速的气候破坏是对流层对污染者的报复。
在日式恐怖片时代,超自然幽灵无法追踪的传染性与病毒式传播的不可思议的技术条件之间存在着相似之处,黑泽清首先在《X圣治》(1997)中用汗湿的双手抓住了这一点。一连串毫无关联的神秘谋杀案及其毫无动机、莫名其妙的凶手令一名警探(役所广司饰)苦恼不已,他精神分裂的妻子只是他无法理解的现代生活疯狂的一个象征。最终,这几起凶杀案隐约与一个健忘到令人抓狂的无名男子(萩原圣人饰)有关,而这个人可能是,也可能不是某种处于催眠状态的精神病患者。但是,这些谋杀案之间的联系及其对应的责任所属却始终不为人所知,各种暗示相互关联,通过不可知的渠道不停盘旋缠绕。

《X圣治》
黑泽清从不喜欢通过解释来粉碎令人困惑的谜团,他后来拍摄了一部可能是互联网时代来临之际新卡夫卡式焦虑的终极之作:2001年的《回路》,该片更新了《午夜凶铃》在录像带时代的屏幕恐惧,探究了网络本身是一种无法插入的接入点——无论是物理意义上的还是虚拟意义上的——通往死亡领域的概念。或者是更黑暗的东西:在黑泽清及其令人不安的讲述中,有着许多接口的新型电脑是各种纯粹自杀式恐怖的闹鬼窗口,它们控制着自己。这也许是一种「卢德分子」所持有的理念,但我们坐在椅子上都能感受到,我们的屏幕与一个虚拟的阴影地带紧紧相连,而这个世界对我们的决定有更大的影响力和控制权。与《午夜凶铃》一样,《回路》也暗示了一种令人不寒而栗的形而上学:这两部影片都围绕着一个未知的、电子式的恶意领域在按自己的计划行事而展开。毕竟,虚拟世界几乎就是一个星界,对黑泽清(他还将自己的剧本改编成了小说)来说,这是一个渗入我们世界的地狱般的另一个世界。最终,虚拟吞噬了我们。还有什么比这更现代的吗?如果卡夫卡和贝克特都能看到如今的互联网生活,他们或许能完全理解这种去人性化的技术迷失。
清水崇导演的《咒怨》(2002)和《咒怨2》(2003)在某种程度上更进一步,将幽灵式的病毒传播喷射到各处。监控录像、电话、汽车甚至影印机等设备都受到了干扰,其他一切也是如此;剧情中的复仇之魂的传染范围超出了最初发生原住民谋杀案的房子,随着更多的受害者站出来,「怨恨」像蚂蚁一样滋生。虽然从本质上讲,这种设定与日本更早的新浪潮电影有更多共通之处,例如其灵感主要来自经典的民间复仇鬼故事《四谷怪谈》,但《咒怨》的病毒性给人的感觉完全与时俱进,甚至可以说是先知先觉——这部电影是有史以来最可怕的流行病寓言之一,比新冠疫情的出现早了18年,而且足够任性,可以纵容真实传染病不可预测的重叠和变异,而不是保持其类型情节的整洁和易于解析。没有安全的地方,甚至(特别是)医院的产科病房,清水崇对于氛围营造驾轻就熟,包括他那简洁的横向镜头移动,让紧张的气氛一秒接一秒:我们要去哪里,当我们到达时那里会有什么?《咒怨》就像病毒一样催生了多部续集,并始终把握着世纪末父母焦虑的脉搏,是一部关于未知的未知的研究,也是一部关于现代特权和假设下的不安的研究。

《咒怨》
总而言之,日式恐怖片是电影文化的一个重要时刻,当一种普遍的社会焦虑感被低俗作品创作者先于其他人诊断出来时,全世界都认识到由此产生的电影折射出了一种隐秘但不可否认的感知/情感真相。这些电影对日本文化中的社会危机和性危机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它们与新浪潮的前辈们有着直接的联系,共同展现了一个处于长期危难中的国家的广阔前景。不过,这些新近电影的关键区别在于,它们揭示了我们现在所处的恐慌环境。在互联网发展初期,当西方学者为网络虚拟地球村的可能性而陶醉时,日本人却看到了一扇黑暗的大门正在打开。可以说,我们已经得到了警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