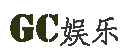二舅故事的神秘魅力:猫、老虎与被雨淋湿的狗狗的隐喻解析
二舅的故事是一个好听的故事,它确实治不了谁,但确实也可以好听。我不认识二舅,也不讨论真实的二舅。我想先聊聊这个好听的故事,再谈谈我所认识的生活中的我们自己。
好故事:猫,老虎和被雨淋湿的狗狗
猫
猫的诱人在于捉摸不透,它从不告诉你它怎么想。二舅在故事里行事潇洒,但几乎一语不发,每言必短而意味深长。作者采用远观的第三人称视角,为主人公的形象填充了诱人的神秘感。我们听不到他展露天才时自鸣得意,遭遇横祸时言悲谈恨,归于平淡时的碎语杂念。这些本都能把他拉回现实,拉回平凡的你我中间,但作者用禁音键切断了它们。
模仿猫的神秘,还要让事情发展中的逻辑联系缺席。要么是天降横祸的一针和鬼斧神工的手艺,要么是说走就走的北京和闷声掏出的房款。我们的视线时而紧随,时而又迷失,这些画面和声音的缺位给予了每个人任想象恣肆的画笔,于是他的形象在叙事中逐渐遥远,添一些抬捧,加一些晦涩,绘一些期许,染一些悲情,达无限深沉、神秘,直到形象抵达饱满的高潮,二舅已经很难再开口了。圣人应该收多少钱呢?仙女怎么吃臭豆腐呢?神像又该说些什么呢?我想这世上已少有配得上二舅形象的话了。
故事中最接近普通人的部分是乱糟糟的爱情桥段,它有些无趣,有些随意,令人摸不着头脑,但借所有涉事者的缄默升华出了深沉的意味。有人能欣赏出浪漫奋身,有人会评价为不羁洒脱,有人总结是苦难的反复。但要我说它只是普普通通的乱糟糟的生活,换你来也是一样乱糟糟。料加到位了,烤鞋底都好吃。
老虎
故事的主角必须是骄傲的虎,因为引人入胜依赖不了人与人间的同情,而要靠向往和代入。二舅必须是年级第一,必须手艺出类拔萃,必须幸得首长亲近,必须是全村人的生存依仗。只有天才不得志的故事才能深深地吸引我们,因为我们是如此需要这样的故事来抚慰自己受伤的心灵。我们每个人的自恋情结都吸引我们去造设自己非凡而杰出的一面,但现实又持续提供给我们充沛的打击,于是无法接受自命不凡与无人理睬之间裂痕的我们,便急匆匆地浸入这个故事里,找到如阿德勒所言的“可怜的我”式精神抚慰。
作者说二舅治好了他的焦虑,自然是以二舅的奇迹才能与苦难人生之间的鸿沟为衬,勉强接纳了自己相对浅窄的心灵裂痕。这里能有什么“二舅精神”呢?我想中国不会缺少某一位大爷、三伯或四叔,拥有少时平庸的成绩,中年倒霉的运气,晚年碌碌的生活,不吭也未怨地在村落里穷尽了一生吧。天下悲惨之事不罕有,苟活之人俯拾是,苦怨之声多未发。很多朋友也提到了这一点:要寻得这种精神,其应是如野草一般遍地有之,而何苦颂为腊梅之高品。
命运倒是很公正的,或者说毫不在意的,它不会看你我平庸就少分一些苦难。你可能会悲催,我也可能很倒霉,你我的勇气本来就配得上同样的肯定。
狗狗
狗狗的意义要比狗还进一步,它指向无条件的善良,可靠和可控。我们原本知道人是狡黠的,是应当在竞争抢夺中展露出他的筹策与机巧的,但在这个故事中它踪迹全无。二舅所有的胜利都干净公平,所有的失败都时命不济。二舅是慈父,是孝子,是才子郎君,是村人依仗,他是你能想到一切高尚的形象,只因为他是一个失败者。当人不得已将胜利让出,就只能将道德的至高感作救命稻草般紧攥,而追逐这根稻草的哪里是二舅,分明是听故事的你我。
正如我们需要猛虎的形象来寄托自恋意识,我们也需要爱宠的形象来寄托附生的讨好意识。我们常常陷入有力使不出的境地,又无法接受与成功就此失之交臂,便希望寻求另一种意义上的胜利:收起的攻击性是一种忍让,退后的行为是一种高尚,即使是失败也可以沐浴道德的光亮。多么动人的光亮啊,可是为何还未有人来赞赏呢?我们一遍遍地在深夜问这样的问题,奢望着夜幕能将那微暗的光,再衬得明显那么一点点。
明明是二舅的故事,怎么你却胸臆难平,又感怀万千呢?因为它唤起的那份悲伤,一定是你自己的悲伤。
被雨淋湿
二舅自然治不好任何人的焦虑内耗,因为焦虑源于自命不凡与生活挫败间的落差,而这个故事正是以相同的落差诱人入怀。读者尽可以在比对中得到安慰,但无法得到任何应用性的指导,因为故事中有另一个不可替代的要素:残缺,我们完美寄托中的最后一环。
被雨淋湿不是一种状态,而是一种遭遇。掉进水坑的狗狗或者游泳打湿的狗狗就无法引起等量的同情,因为前者指向自身能力的堪忧,而后者归结为自负责任的行动,两者都无法将责任完全转移。天降之灾则不同,受害是一切失败的最优归因。壮志未酬一定是天公不作美或恶人强作祟,一位完美的盖世英雄可以在这样的情节中拥抱他的失败而又毫无愧色地收获掌声,这就是“可怜的我”和“可恶的他人”为我们的自恋情结提供的完美答案。
如前所言,世上不乏正在出演二舅后半生的三叔和四伯,我也不相信他们之中缺少才能杰出之辈。但他们的故事通通索然无味,因为其中“不幸”缺少了天降的苦难。若是喝酒骑摩托摔坏了身子,或是高考失利断送了前途,要么在事业挫折中遭受了等量的创伤,二舅听起来还有那么英雄吗?如果我们向往的是纯粹的挑战苦难的勇气,那么“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就不该比“茅屋没搭好搞砸了歌”更加悲壮,因为在仓皇中求生的艰难是等同的。
所以健全者无法成为一个英雄,因为他永远要为未达完美而自负全责,他看起来是完完整整的,于是在完整的检验下他永远背负着各处的瑕疵。而不幸者却又有幸是破碎的,我们一早接受了他的破碎,欣赏起其中可取的图块来。我们拾起他的快乐,说这是多么纯粹的快乐;我们捡起他的勇气,并评价说这真是一块完美的勇气。
我曾经忽有奇思,若是我失去一条臂膀,我坦诚地说我此刻的人生焦虑几乎可以一卸尽空。我明白残疾的苦难并不是我配如此轻言的,它们残酷地将生活卷入更沉重的困境,但我想指出的是,我当下的全部焦虑的确都浮系于我如此健全完整而有力却未能争取到的那顶王冠之上。
丧失的生命:内耗
王冠的意思,就是指世上只有这一顶王冠。但我似乎看到每个人都头顶着王冠。有的看起来还是个底架,有的大概没涂明白,有的还在来回转手,但至少他们每个人都自称拥有。人人都有的王冠早已失去了王冠的意义,但好像也没人在意。一只灵长类奔波追逐着一个不存在的东西,我想除了焦虑和空耗,还该有什么感觉呢?我一转念这事好像又眼熟,像极了一条驴和一根胡萝卜的固定搭配。
断裂的外化
内耗就是没能对外做功的能量,其精髓不在于耗,而在于“内”。一方面它把遗失的耗散转为对内的自伤:机轮空转,烈火空烧,有一拳满贯的力打不出去又卸不下来,沉闷地落在了自己的心里。另一方面它隐藏于内,从不示于他人。有时它只是想前进时的原地踏步,有时又是愤气闷堵时的拥塞窒息,有时是溺死时的扑腾挣扎,但这一切的惊涛骇浪,在身畔人的眼中不过秋毫一闪。没人能觉察的东西,也就没人会来解救。
一切来源于送不出的能量。在自然的运行逻辑下,人将脑中产生的念头依靠身体实施,完成生命力的外化。而在我们这里,两步之间出现了断裂,我们生出了太多在客观条件下无法实施的念头。玩过赛车游戏的人应该可以记得起点线常见的画面:按下前进键时车轮已经开始转动,但由于刹车锁死,轮胎会在地面空转而留下烧焦的印记。结论是我们出了问题,要么是动力错位,要么是限制过度。
错位的动力
交通和通信技术的发展送给了我们太多不合时宜的动力。这个世界的效率已经如此之高,以至于它留不下给年轻人成长的时间。无论在艺术、科学还是游乐题材中,我见到太多初出茅庐者的视频被批评否定的弹幕评论淹没,就因为他们和随处可赏的大师作品“尚有差距”。从前每个物种都等得及春华秋实,现在的韭菜只允许一夜成材。适合新生儿成长摸索的空旷、留白和朦胧没有了,瞬息之间全球的事物的画面和声音都奔涌汇一,它们棱角毕现,相互倾轧,嘈杂凌乱。从前的人会在田野里成长为农夫,会在山林里成长为猎户,会在大海边成长为渔民,而我们在网络的爆炸声中,正成长为碎裂的飘萍。
高效率在众多场合削减了时间,我们对时间维度的掌握也被一并削去了。夏虫本不必语冰,夏虫活得也挺舒坦;如果还能活到变冬虫,那真是划得来。但人却在此面对着重大的危机。一个年轻人在耕种时就已经读到收获的知识,在屏幕中见到花叶的样貌,还有老一辈的人向他炫耀的花环与果实。随着通信效率暴涨,这些物品的形象越发地真实鲜明,以至于他甚至难以区分画面和实体。他站在春日的田野上,眼中却满堆着PS过头的秋日的大丰收;他热切地伸出手去,喉咙却更加干渴。他会不会就这样死在未耕的田垄上呢?我们不知道,也不关心,因为这只是越来越拥挤的土地上一个被自然淘汰者的个人命运。
数据的枷锁
互联网说是印钞机,我寻思印那些钞可能买下了不少人的灵魂。我们很自然地讨厌大数据,因为它做的就是将我们“非人化”处理。无论具体操控的是什么,指标无非是用户数量或营业额,里面没有你的喜好他的情感她的健康,只有一蹿再蹿的数字。我们被学校用考试分数描述,被导师用论文数量描述,被公司用员工价值描述,被家长用步入人生正轨的时间表描述。在一定程度上,数据正在统治我们。作为人,我们看二舅视频了解一个故事,催生某种情绪,谈论一些感想;但数据统治之下,我们看到众多的活动都在为数据服务:人们在讨论视频的播放量和成功,人们在讨论爆火蹿红的原因和技巧,讨论二舅签约直播的话可否厚非。我们热热闹闹地在给情感和故事商讨量化标准:一个故事,一个形象究竟是多少播放量,是多少收入?高情商的评价是,这不应该属于人自然天性中对事物的理解和掌握方式;低情商的评价是,我觉着这哪是人干的事。
我们也在丧失对空间维度的掌握。从前人是可以走无数条道去罗马的,如今我想进清华只有一个分数线。本来这个世界是复杂的,奇怪的,每一样新的物件,新的地点,新的生物都是奇迹般构成的,人不能理解的。人可以吃ABCDE,做12345,在任意的天地,活任意的时长。生活一点也不好,但一切都无所谓。你尽可以往南,往东,再往西,一路上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数字。而现在我们把一切都计算好了,每一顿饭和每一晚眠都标好了价,人生目标也是一个蹭蹭上涨的数字,甚至人自己也成为了数字。所有人都在努力把其他人化成一串数字,这对于人际关系和情感的影响自不必赘述,另一方面,人群熙攘的大地逐渐变成了数字细密的版图,而具有绝对尺度的数字进而建起了坚固无情的壁垒。考多少分数的人进如何的学校,找到如何收入水平的工作,再搬入如何房价的社区,在这个过程中形成如何的人际圈,这整个过程代代重复,以至于我们对这个循环中的每个数字都如此亲切熟悉,超越了水果的酸甜,鸟鸣的声响,叶片的触感,阳光的暖意。如今的我们有什么五感和八方呢?价格告诉我什么是香,经济决定了哪里更美,我们哪有什么选项,我们只有一个数字。高考选专业时,我说不出我喜欢什么事物,因为我事实上不熟悉它们任何一样。可是我熟悉分数,我只能喜欢分数,于是我选了需要分数最高的专业。现在想来,我不确定是我拥有这六百多分,还是这六百多分主宰着我。
"整点薯条"曾给这个绝望的框架撬出了些裂痕。“整点”卸下了我们对未来的重负,提出了一个脚踏实地的行动,让生命力得到伴随充分自信力的外化。“薯条”打破了价值的衡量,它让一个黄红相间的,油滋滋脆香香的形象释放了独特的幸福感。我不好定义它是什么,但我想它的美产生于它不再能用数字描述的那一刹那。
模仿的生活
这世上大多数人就是活得“尴尴尬尬”的:他们知道夫妻应该恩爱,亲子应该融洽,所以他们“模仿”。对,他们模仿自己看见和理解的那种家庭关系,他们确实想要,但因为胸腔里并没有那一颗真心,所以呈现出来的效果就是:令人尴尬。
@琉玄()
我们一方面不会处理时间,无法忍受“想要”和“立马得到”之间的时间差距,另一方面不会处理空间,无法接受A美,B也别致的多元价值尺度,这就催生了内耗:在客观条件不成熟的时机,向当下不合理的方向奋力地空转。
关于未来的焦虑都有时间感的缺席:我们总是虚要立即拥有苦练者的技能,马上摘取与久耕者相同的果实。所有的光鲜亮丽都被迅速高效地展示在我们眼前,我们却无法跳过那漫长耕耘的光阴来顷刻回应,时间的不对等将我们撕裂。
关于竞争的焦虑则是空间感的缺席:因为颜值和身材可以打出分数,我们就忘记了每个人的身体都有独特的可爱之处,所谓“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行业本不分高下,但分数线和收入早划好了严格的贵贱。生物本只有无数种中性各异的降生,存留和离去的形式,但我们将其收拢到了一个数轴之上,任凭自由的生命力被挤压其中,缚在一串数字下无助地挣扎。
向着死胡同追求着一蹴而就,无非走向的是空耗、撕裂、伪造或是偷取。像生命中的大多数事情一样,我们不是选其一,而是每项都沾点。空耗蹉跎岁月,撕裂走向灭亡,而伪造和偷取需要无休止的维持——我们终成为了面具的奴仆,为它奉献了更多的空耗。上一章所写的就是三副如此的面具:猫,老虎和被雨淋湿的狗狗。这事猪听了都会觉得好笑:一个人,怎么能又同时是三种动物?而我们倒没想过去咨询它,只是忙于扮演出尖利的爪牙,扮演出神秘的步态,扮演出温顺与讨喜,再在卸下戏装的深夜抓紧时间哭一鼻子。
残缺的新生
你能成为兔女郎吗
你能成为飞行员吗
你能成为偶像歌手吗
你能成为用必杀技拯救世界的英雄吗
成不了
或许能行也说不定
但是眼睛老是注视着不存在的东西是不行的
把希望寄托于自己的别的可能性
这种虚无缥缈的东西之上,这正是万恶之源
你必须认同只能成为如今的你的自己
《四叠半神话大系》
人类造了不少的偶像,糟就糟在他们是按自己的外形造的。偶像一旦出生,健全就成为了罪过。你也是个人,你为什么不像维纳斯和大卫一样健美呢?你也是个孩子,你为什么不像别人家的孩子一样乖巧呢?如同人对时间和空间掌控力的丧失,人也逐渐忽略了健全和完美之间还存在“有限”这一差池。或者说,与完美相比,人有太多未能轻易可见的残缺。这些残缺注定了我们将自己雕琢为偶像的努力尽是空耗,但我们却在外形的相似面前苦思不解。
相较完美,我只有一个没啥性能的大脑处理器,一个进者多漏的知识存储区,一些飘忽涣散的注意力,一具平躺都嫌累的年轻身躯,和在世界极狭窄的一隅,与极有限的一些人相处,度过了极有限的一些年月的人生。我能凭借这副身躯成为奥运冠军吗?我能凭借这个大脑成为爱因斯坦吗?我能凭借这些稚嫩的知识功底和平庸的创造天赋成为艺术或是文学大师吗?那么,我可以凭借如此浅薄、如此偏颇、如此普通的生活塑成的如此有限的自己,成为那个支配自己至今的完美的偶像吗?
偶像的问题在于,他各方面都能做对,每一件都能做成。与之相反的,当我理解我是如此有限而残缺,我就能明白一些有趣的道理:我可以做一些事,我可以做成功,也可以做失败。我可以认识一些人,我可以被喜欢,也可以被讨厌。我可以了解一些知识,也可以完全不懂。我可以学习一些技能,也完全可以学不会。我可以用好一些时间,也可以完全浪费了一些。我可以吃亏,可以大意,可以笨手笨脚,可以错失错忘,下一次也许能搞对,可没有下一次也没关系。这些事情教小学生太幼稚了,但对成年人来说正合适。我们在焦虑下自我折磨:“真惨,我是个废柴。”而在追求解脱中大声抗议:“真棒,我是个废柴!”
作者归纳了一个俗套的二舅精神:把人生的烂牌打好的精神。我自然不敢苟同。牌好牌烂,打好打烂,又由谁来说准呢?我们在焦虑与内耗中如履薄冰,兢兢度日,就是害怕在天下人面前把手中的好牌打烂。可是真的好牌,怎么能那么容易打烂呢?事实是我们在迎合着他人期许的同时,早清楚自己这里烂牌不下几组了。要我说,一来谁没又几张烂牌呢?人常常是自己明白是装的,看别人又全信了;二来要端正自己的身份:你没法开挂,不会出千,怎么局局就都得让你打好呢?我的一个朋友讲得很好,事情只有一个动词就是做。在这里牌只有一个动词就是打。人生牌桌,大大方方地打,堂堂正正地输,反正结算时你也该下桌了。走时哪怕输剩了裤头,还是拍拍屁股,利利索索,也不妨骂骂咧咧。
老人与海:活着
视频在末尾自然提出了这样那样的畅想:以二舅的才智,如果没有那几针,当然能做工程师,住城市里,有好房子。这个畅想既是索求安慰者们最爱的温柔乡,又恰证明了世上没有什么绝世英雄竟不得志的传奇。因为做到这样的人太多了,他们每个人都可以是二舅,但他们的故事没几个人会爱听。这个故事好听不是因为二舅是二舅,而是苦难如此至,旁人如此释。这不是二舅的故事,而是苦难命运的故事。
另一个朋友说,二舅的故事给她老人与海的感觉。经由命运摆布凌辱却不失掉挣扎撕咬的韧性,这是何等浪漫的英雄主义。但同样的,老人与海也不是老人的故事,而是海和人类的故事。“你尽可以消灭他,可就是打不败他”讲述的丝毫不是人向自然发起骄傲的挑战,再壮烈谢幕的故事。它是拥有绝对力量的海无情翻覆,而人在其中挣扎苟存的苦难故事。大海、自然或是命运从不会给任何人一瞥,它只是肆意而无情地行进。野蛮狼狈地活下去,就是每个生物本能而唯一的行动,它不值得任何歌颂和赞扬,因为它就是生命力原原本本的形象。如果它也能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就意味着我们在献身于建构社群巨物之时,自身的生命力已然耗尽。躲在毫无生气的躯壳中,为了一些木偶与粉饰啼哭的灵魂,也就不必与其论风雨了。
好在它是一个海与人类的故事,任何个体的迷失都不会改变人类在存亡关头重现的作为生物的生存渴望。海明威用最干练的毫无辞藻的语句,勾勒了人类最原始,纯粹的生命力。沉默的,孤独的,强韧的,苦难的,狼狈的,挣扎的,潦倒的,喘息的。老人不是怀志奔忙的你,不是灯下闲坐的我,他是我们血液里的一股力量,在当下掩没得很深,但也始终扎根得很深。
暴浪翻涌,无情的巨力尽毁我们优美的虚饰和伪面,涤荡出裸露的残缺与伤痕。我们在这肆虐的波涛中失去体面、失去愁怨,也失去焦虑。而这股力量终于苏醒,一个人类的形象沉默着,孤独着,坚韧着,痛苦着,狼狈着,挣扎着,潦倒着,喘息着——活着。这就是二舅与苦难的故事,老人与海的故事,活着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