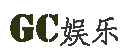《弘明集》中因果报应论争述评(刘立夫)
因果报应说是佛教的一个基本教义。在印度佛教中,它常常被称为业报轮回说。汉魏以来,随着佛教的不断流传,业报轮回说又同我国固有的善恶报应观念结合起来,深入到民俗信仰和士大夫的精神生活当中,产生了广泛的作用和深远的影响。与此同时,也引起了一些固守儒家传统的文人士大夫的怀疑和批判。自两汉至西晋,由于佛教在中土的影响较微,问题尚处于萌芽阶段。而东晋及刘宋时代,情况大为改观,围绕因果报应问题的争论成了当时思想界一重大理论问题。随着论争的不断深入,又发展到齐梁之际的神灭神不灭之争。此种争辩在《弘明集》中多有反映。
因果报应、业报轮回、三世报应、或者善恶报应等等,往往被当成同一概念之不同称谓。其实,这些概念的本来意义还是有差别的。回顾中土早期佛教史,亦能够发现此种差别。作为方便,不妨将印度佛教之报应观称为“业报轮回说”,慧远以前之中土传统报应观为“善恶报应说”,而慧远等人发挥之学说称为“三世报应说”。总而称之为“因果报应说”。亦即因果报应是一总名,其余三者为是个别、特殊之概念。当然,“名者实之宾也”,此种称谓仍为方便的作法。
在印度佛教因果报应说传入中国以前,中土曾流行一种与它相似的善恶报应观念。其基本特征就是“积善余庆,积恶余殃”。此说法散见于《周易·坤·文言》、《尚书·皋陶谟》、《国语·周语》、《老子》、《韩非子·安危》等诸多传统典籍中,既是一种残留在当时人们心中的宗教信仰,又逐渐转化为一种根深蒂固的伦理传统,深刻地影响了中土民众的善恶选择和道德行为,成为政治教化的组成部分。但东汉王充曾对当时社会上流行的鬼神方术进行了深入地批判,其中也涉及当时人们迷信的善恶报应观念。其《论衡》《福虚篇》、《论死篇》、《祭意篇》等多有批评。
从中土善恶报应说的有关记载看,其同印度佛教的报应论虽然在形式上相似,但内容却迥然有别:其一,就报应之主宰言,印度佛教认为业报轮回的主宰力是“业”本身,人的作业会在三界中流转不息;而中土传统的报应说主张报应的主宰力则是“上帝”、“天”、“天地”、“鬼神”等等,可统称为天地鬼神,因而主张祭祀天地,祭祀鬼神,以求福避祸。其二,就报应方式言,印度佛教比较复杂,有前世、今世、来世三世报应,轮回无穷,且有五道或六道等报应层次之差别。而中土传统的看法就比较简略,一般主张在生为善积德,或者祭祀天地鬼神,就会得到善报,否则就会遭罚,不涉及三世轮回与六道等关系。其三,就报应的主体言,印度佛教主张自我承当,自作自受,前生造业今生得报,今生造业来生得报;又因人之肉体会自然死亡,故于逻辑上乃得出灵魂承担来生受报之结论;而中土传统报应的主体承当者有两种:一是今生善恶今生受报,一是祖先的行为于后代或亲人代受。
业报轮回说随着印度佛教的传入在中国逐渐流行。宣传这种思想最主要的方式就是佛经的翻译。相传汉代最早来中国传教的安世高就翻译了宣传因果报应的《十八泥梨经》、《阿难问事佛吉凶经》、《罪业应报教化地狱经》等经典(今《大正藏》无载)。由摄摩腾翻译的《四十二章经》当是某些小乘经典的节译,经中也记载了大量的关于因果报应的言论。另在早期的僧传著作中,亦常常夹杂着有关高僧对因果报应的说法的记载,此为宣传因果报应说又一重要途径。例如,《高僧传》卷一《安清传》中就有大段以神迹传教的文字,《高僧传》卷一《帛远传》也有类似之记载。上述两初记载都以高僧大德的现身说法来应验因果报应的“信而有徵”,而且当事人都有神通,前知宿缘,因此,面对死亡,毫无畏惧,安世高“申颈受刃”,帛法祖“欢喜毕对”,都愿意用自己的生命来换取夙敌的超度。这在当时看来,无不惊世骇俗。
因为印度佛教的业报轮回思想对中国人来说还相当陌生,所以当初人们多迷惑不解,遭到怀疑甚至批评。《牟子理惑论》上有云:“佛道言人死当复更生,仆不信此言之审也。”“今佛家辄说生死之事,鬼神之务,此殆非圣哲之言也。”袁宏《后汉记》卷十曰:“又以人死精神不灭,随复受形,生时所行善恶,皆有报应。”“善为宏阔胜大之言,所求在一体之内,而所明在视听之外,世俗以为虚诞。然归于玄微深远,难得而测。故王公大人观生死报应之际,莫不矍然自失。”范晔《后汉书·郊祀志》曰:“又精灵起灭,因报相寻,若晓而昧者,故通人多惑焉。”
汉晋以来,中土人士把佛教的业报轮回同“精灵起灭”和传统的生死鬼神问题联系起来。所以,在开始的时候,人们也用祭祀鬼神的办法以求得佛的保佑。从上述各种评论的措辞来看,人们并不完全理解佛教因果报应的内容,虽然人们已经有一些模糊的认识。当然,越是到后来,对它的理解就越清晰。《晋书·羊诂传》卷三四晋人羊诂转生的故事可以看成是印度佛教业报轮回思想深入民间的一个例证。这个故事对轮回的理解已经与印度的原意无差。东晋居士郗超作《奉法要》,对佛教的基本教义、教规作了通俗而简要的论述。其中有对三界五道的论述,并且引用佛经“心作天,心作人,心作地狱,心作畜生”的思想,认为“凡虑发乎心,皆念念受报”, 已经比较准确的把握了业报轮回的思想真谛。
《高僧传》卷十五曰:“(慧远)每至斋集,辄自升高座,躬为导首。先明三世因果,却辩一斋大意。后代传授,遂成永则。”《弘明集》卷四《答桓太尉》曰:“大设灵奇,示以报应,此最影响之实理,佛教之根要。今若谓三世为虚诞,罪福为畏惧,则释迦之所明,殆将无寄矣。”
由以上可知,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发展过程中,业报轮回说成了佛教教义的最重要的方面,不仅世俗人将它当成佛教的核心,教内人士也把它看成是佛教的“根要”。但是,人们对业报轮回说也表示了极大的怀疑,由此引发了后来关于因果报应的多次论争。
印度佛教的因果报应思想虽然在中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毕竟不符合中国的传统观念。人们当初是“骇其奇异”,认为它“宏阔胜大”,玄微难测,虚诞无证,因此“通人多惑”。但因果报应的思想毕竟逐渐深入到中土社会的各个阶层的精神生活当中,影响日益加深。如果说在晋代以前,中土思想界对佛教业报轮回说尚处于疑惑之阶段,那么,从东晋开始此一问题则被提到议事日程,引发多次重大争论。此种论争可划为两大阶段:第一阶段在东晋,代表人物有罗含、孙盛、慧远、孙绰、戴逵、桓玄、王谧等,《弘明集》载集了其主要文章,如罗含《更生论》、孙盛《与罗君章书》、孙绰《喻道论》、慧远《明报应论》、《三报论》等。值得注意的是,在有关的争论中,双方围绕的常常不是印度佛教的因果报应说,而是中土传统的善恶报应论,或者双方往往把两者混杂在一起,反映了争论双方对业报轮回理论本身的模糊不清。第二阶段发生在刘宋时代。主要代表人物有何承天、宗炳、颜延之、刘少府、慧琳等。《弘明集》收录的文章主要有:何承天《达性论》、颜延之《释达性论》以及两人针对《达性论》的几封往来信件;宗炳《明佛论》、何承天《与宗居士书》以及两人的往来信件。此外,《广弘明集》补录了与此相关的何承天与刘少府的文章,《宋书·蛮夷传》记载了慧琳的《白黑论》等。
(一)第一阶段之争论
东晋罗含著《更生论》,为佛教的轮回观作了论证,但只涉及轮回,不涉及报应。罗含的观点遭到了孙盛的反驳。孙盛作了《与罗君章书》。后来罗含回书,称《答孙安国书》,继续辩论,但三篇文章都不长,点到为止,论证也相当粗糙。罗含的《更生论》基本思想是认为天地无穷尽,万物的生命都要更替,在无穷的更替当中,新的生命只是旧的生命的循环反复。孙盛针对《更生论》写了《与罗君章书》中仅就两点提出质疑:一是,传统经典多有一物化为异物之记载,未说能够还原成原来的形体的。二是,形体既然粉散,精神亦是如此。粉错混淆,各失其旧,不可复原。
《更生论》是对印度佛教业报轮回说的一种极为初浅的理解。他企图以中土传统的思想为基础来论证万物生死的轮回而不是业报的轮回。他把人的生命(加上与形相“偶”的神)、实际上是传统的“气”看作轮回报应的主体,认为只要证明生命轮回就证明了业报轮回,并且不自觉地借用庄子的齐物观来附会业报轮回说的宗旨。也就是说,罗含仅仅是想“证明”轮回的可能性,实际上他对佛教学说的了解还存在相当大的差距。孙盛不同意罗含,根据传统之自然观和感性经验进行驳斥。
《弘明集》卷五收录了东晋名僧慧远的一组文章,其中包括《明报应论》和《三报论》两篇关于因果报应的文章。慧远的理论水平跟罗含相比已经有一个质的飞跃。罗含毕竟是官僚士大夫出身,加上时代比慧远要早,佛学功底相对不足;而慧远早年研究孔孟老庄,后师从道安,精通佛教经典,因而能够将内典外教融会贯通起来。慧远结合中国传统的善恶报应说与印度的业报轮回说,系统地论证了三世报应说,在中国佛教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明报应论》全称《答桓南郡明报应论》。这是慧远就桓玄有关业报轮回的疑问所作的解答。论文以书信的形式出现,桓玄的问答在这封信中也保留下来。
桓玄一共提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佛经以杀生为重,地狱斯罚,冥科幽司,应若影响,余有疑焉。”理由是,人的形体由四大结合而成,神寄托其中,因此,杀害一个人的生命相当于消灭了天地间的一部分地水风火,于神毫无妨碍;既然于神毫无妨碍,哪里会有什么报应?第二个问题是,“万物之心,爱欲森繁,但私有有己,若因情致报,乘感生应,则自然之迹,顺何所寄哉?”一切众生都有欲望情感,为自然之准则;而人不过富有情感和思虑而已,如果情感会导致报应,这同自然的法则相符合吗?第三个问题是,“若以物情重生,不可致丧,则生情之由,私恋之惑耳,宜朗以达观,晓以大方,岂得就其迷滞,以为报应哉?”贪恋生命是众生的本性,如果众生有了欲情,也应该以达观的道理引导他们,岂能用轮回报应来迷惑他们呢?
桓玄这三个问题,涉及到形神关系、人的正常欲望、情感、思虑是否合理以及佛教因果报应说的伦理价值等问题。对此,慧远首先认为佛教的道理“深玄”,必须把握其思想“指归”才行。他认为佛教讲四大结形,正好符合庄子的人生气聚、人死气散的道理。既然人生的起灭皆在一化,那就可以视生命为“遗尘”,心灵翱翔于无穷的宇际,超凡脱俗。如果人的心能够无所眷恋、无所执著,那么,两军交战就好比知心的朋友相聚,本无生命可杀,焉有伤神之理?如此,既无功劳可赏,焉有地狱可罚?慧远认为,问题不在这里,如果能够换一个角度,从有情众生产生的根源和发展的角度去认识,问题就会临刃而解了。就是说,人的身体是“情”感应四大而结成的,有情缘于无明,贪爱缘于有情,有情有爱,便生无穷无尽的迷惑和烦恼。于是,人们私身恋生,患得患失,彼此界限森严,产生善恶的行为,埋下报应的种子。有了善恶,就会有报应,这是必然的规律。
慧远接过桓玄的“自然法则”回答说:“心以善恶为形声,报以罪福为影响。”“心”(实质上是不灭的“神”)蕴涵情,自然就有善恶,有善恶,当然就会有报应。是否受报应取决于人对心的控制,报应是不存在一个外在的主宰力量的。这就叫“自然”。“自然者,即我之影响耳。”并非有一个外来的支配力量,而是人的主体自身造成的。慧远接着连续反问道,既然神以四大为宅,那么神就是形的主宰。为什么?如果神不主宰四大结而成形,人的身体哪会有痛痒等感觉和知觉呢?没有神主宰的感觉和知觉,那么杀人不也就像砍树剪花那样无知无觉了吗?因此,形神虽然是两个东西,但应该是浑然一体的、同步变化的。
最后,慧远说,善恶的根源在于人的心,如果人能够“责心”自反,就可以消除报应。所以,佛陀因为人们的执迷不悟才阐明因果报应的道理,并不是仅就人们的执迷不悟的现象本身而制造了因果报应之说。人们的积习不可能一下子就能够消除的,所以要示之以罪福报应,一旦“情无所系”,就可以晓以大道,用不着再讲报应了。
生活在东晋中后期的戴逵不仅是著名的雕刻家、书法家,也是一个佛教信徒。《广弘明集》补载了戴逵写给慧远的两封信:《与远法师书》和《释疑论》,表达了戴逵对善恶报应的怀疑以及自己一生艰楚备至的悲概无奈。慧远在这种情况下作《三报论》,回答了戴逵的疑惑。《三报论》的副题是“因俗人疑善恶无现验而作”,表明解决这一问题的普遍意义。
戴逵主要观点是说,圣人在经典上讲“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又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而在事实上常常得不到应验。他自己一生的悲惨命运就是雄辩的明证。所以,积善积恶之谈,无非是劝教之言,并非实有其事。
慧远的《三报论》回答了戴逵的疑问。共有三个要点:(一)报应的种类分为现报、生报和后报。现报是现身作业,现身受报;生报是今生作业,来生受报;后报是前生作业,经过二生、三生乃至百生、千生的转世才能受报。(二)报应的主体是“心”(神识)。心只有通过对事物的感应才能体现出来,也就是心是随着各种因缘条件而显现的。人的报应之所以有先后,是因为心感应事物的速度有快有慢。(三)报应虽然有先后差别,但报应的轻重是与人所作善恶诸业的轻重程度一一对应的。这就是慧远三世报应说的基本构架。
慧远接着对三世报应说作了较为细致的论证。在慧远看来,仁人志士立功立德反而多灾多难,命途不济,出现这种反常现象的原因就在于,每一个人在生时所造的善恶诸业就埋下了果报相寻的种子,一旦因缘条件成熟时自然就会表现出来;这样,祸福报应就在六道中轮回不已,有正常,也有反常,阴差阳错也就不足为奇了。而传统经典理论均以一生为限,只凭感觉经验作出判断,这就不可能正确的理解因果报应的道理;如果将内典于外教结合起来,二者正好可以相互补充,儒家圣人不言天命的缺陷可以通过佛教来弥补,可谓殊途同归,圣人弘教的用心不就更清楚了吗?
(二)第二阶段之论争
东晋以后,随着佛教影响的日益扩大,对佛教因果报应问题的认识已经大大地深化了。到了刘宋时代,争论进入了白热化的阶段。《弘明集》记载了何承天的《达性论》,《宋书·蛮夷传》记载了慧琳的《白黑论》,这两篇文章实际上是当时反对佛教因果报应说的代表作。围绕这两篇文章,颜延之与何承天、宗炳与何承天、刘少府与何承天(载《广弘明集》)等进行了激烈的辩论。
何承天的《达性论》文字简略,立论奇特。它不是就佛教报应说的逻辑本身进行批判,而是以传统的儒家三才论,对抗佛教的众生说。《达性论》认为人乃万物之灵长,与天地相参,以仁义立物,在天地万物之中具有特殊而崇高的地位,安得与其他各种飞禽走兽一样视为“众生”?何承天的结论是:第一,有生必有死,形毙神散,“犹春荣秋落,四时代换,奚有于更受形哉”!人与动物是不可能互相转生的。第二,儒家经典上有君子求福,三后在天等说法,但本意是说精微之气升归于天,君子以弘道为己任,而不是宣传轮回报应的。
何承天的《达性论》,遭到了佛教信徒颜延之的猛烈反击,双方以书信的形式往辩难多次。《弘明集》记载了这些通信,它们包括:《达性论》、《释达性论》、《答颜光禄》、《重释何衡阳》、《又释何衡阳》、《重答颜光禄》等共六篇文章。双方的辩论围绕两个中心展开,一是人与其他生命能否同称众生,二是对儒家经典中的鬼神采取什么态度。
(一)关于人与其他生命能否同称众生的问题。颜延之反驳说,众生也就是“含识”的总名,它们的共同特点是都能“了别”万物,与其品德的高低并无关系,称为众生无问题。人与动物比较起来,智慧最灵,至于都具有生命,却没有差别,忌讳众生之名,难逃众生之实。
(二)关于对儒家经典中的鬼神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颜延之反驳说,如果人死如草木,圣人讲“三后在天”、“精灵升遐”岂不自相矛盾?如果不同草木,精灵升天,三后在天不正是归因于他们的善报吗?岂不证明佛教的轮回报应是存在的。
何承天还与宗炳争论慧琳的《白黑论》。宗炳与何承天关于因果报应的争论主要体现在宗炳的《明佛论》一书中。另外,《弘明集》卷三(金陵刻经处本)有《难白黑论》,内容包括何承天《答宗居士书》(三篇)宗炳的《答何衡阳书》(二篇),可以相互补充。宗炳的《明佛论》以及上述几篇书信,都是就慧琳的《白黑论》而发的,其中涉及的方面很多,而关于因果报应的争论主要是现实生活中报应是否合理的问题。
何承天根据日常生活中诸佛不显神力的现象,特别是秦赵长平之战白起、项籍一日坑杀六十万众的事实,驳斥佛教以慈悲为怀的虚幻不实以及因果报应的不合理性。这是一个用实证无法回答的问题。
宗炳是这样论证的。“今所以杀人而死,伤人而刑,及为缧绁之罪者,及今则无罪,与今有罪而同然者,皆由冥缘前遘,而人理后发矣。”(《明佛论》)今世杀人犯罪,有的受罚,有的不受罚,道理是一样的,都是前世冥冥中定下的缘分,至于是否受罚,要看社会条件是否成熟。前因后果还是存在的。所以,“夫幽显一也,夫衅遘于幽而丑发于显既无怪矣,行凶于显而受毒于幽,又何怪矣。”(《明佛论》)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间上有先后错位都不应该感到奇怪。至于当时人们常常引用的长平事件和项羽坑杀秦卒是否符合因果报应的逻辑的问题,宗炳作了令人吃惊的解释。他说:“今所以称佛云诸法自在,不可思议者,非曰为可不由缘数,越宿命而横济也。盖众生无量,神功所导,皆依崖曲畅,其照不可思量耳。”诸佛有神功济物,但不可越宿命而横济,还要按照人的宿业的具体情况而定;有的人并不会像六十万众那样,遭到坑杀,而是佛光普照,处处得到诸佛的护佑,并能亲自目睹佛国的崇高,原因在于他们世代信仰佛教,修持佛法。而那些前世不修佛法的人,今世即使“清若夷、齐,贞如柳、季”,又怎么能够“感而见佛”呢?六十万众受坑于一日之中,原因就在于他们吃了动物的肉,他们的道德品质虽然相异,但杀生这一点是完全一样的,故受害于同一天也是说得过去的。宗炳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办法是:“若在往生,能闻于道,敬修法戒,则不必坠长平而受坑马服矣。”(《明佛论》)
《广弘明集》补载了何承天的《报应问》和刘少府的《答何衡阳书》,从逻辑上看,是这个争论的继续。《报应问》提出了两种判断真理的标准:一是直接验证,如用“璇玑”(天文仪器)观测日月的运行变化规律;二是间接验证,用可见的去验证不可见的(“取符见事”),由近及远,由显及幽。但是,因果报应说能够经得起这样的验证吗?鹅吃青草,游清池,长大了被人杀了吃掉;但燕子专吃飞虫,人们反而喜欢它,岂非杀生无恶报,为善无福应吗?那么,由近可以推远,人食了牛羊的肉又有什么理由遭到报应呢?所以,佛教讲报应,并非真有什么报应,只是“假设权教,劝人为善耳”, 与实证无关(《广弘明集》卷十八)。
回答何承天这个反问的是刘少府。刘少府认为三报论是幽明之理,非见闻所能验证,而何承天用世俗的推论去诘难它,真是迂腐之极。他说,人之食鹅与燕之食虫,对鹅虫而言是现世受报,而人燕之报是来世报,“善恶之业,业无不报,但过去未来非耳目所得,故信之者寡,而非之者众”。(《答何承天》《广弘明集》卷十八)报应都是有的,区别在于时间的早晚。
以上是晋宋之际有关佛教因果报应论争之大势。
因果报应本为佛教之重要教义。其中的业报轮回与天堂地狱之说目的在于说明人生苦难之根源以及摆脱此种苦难之前途,即要人们认识到世俗的思想和行为会导致无穷尽的痛苦,只有遵循佛的教诲修持佛法,才能摆脱烦恼,脱离轮回,觉悟成佛。而在早期中国思想界争论不己的报应问题已经转变成了一个世俗的伦理问题,它要解决的多是现实经验世界的人生矛盾,即为什么积善得殃、凶邪致庆的问题。实质乃是人的命运问题。现实生活中的富贵贫贱、生死寿夭、吉凶祸福到底是由什么决定的,个人道德上的善恶与命运中富贵穷达为何不一致,传统文化早已关注。这就是中土传统的善恶报应说及与此对立的命定论,二者皆有着自身无法克服的矛盾。善恶报应说作为一种劝善的说教反映了人的美好愿望,但现实生活中善恶不得其报乃至相反的事实比比皆是,子孙受报的说法也屡屡与历史事实不符。司马迁、王充等人对此进行了严肃而深入的批判。而命定论如孔子所谓“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王充所谓“元气论”,相信人在命运面前无能为力,只能乐天知命,安于现状,这就取消了人的主观力量和社会责任,违背了儒家传统的自强不息之精神,也难以为正统之思想家所接受。
在传统学说千疮百孔的时候,佛教的业报轮回说为之注入了一股新鲜血液。在前述中土思想界的争论中,慧远的三报论最具有典型性,贡献也最大。中国佛教的因果报应思想之所以能够深入人心,产生广泛而深远的社会影响,慧远功不可没。在晋宋时代有关佛教报应说的争论中,佛教一方总体上处于主动有利的地位,除了政治上的原因以外,慧远的三世报应说的理论水平和层次要明显高于对手,而颜延之、宗炳、刘少府等人也直接继承和发挥了慧远的理论成果。因此,我们讲中国佛教的因果报应思想主要的就是经过慧远等早期思想家们整理过的三世报应说。这个理论综合了印度业报轮回说和中土善恶报应说,理论基础几乎全部是印度式的,但它所要解决的问题却又是中国的。它具有极大的弹性和圆融性,克服了中土囿于视听、感性经验而缺乏视听之外的玄想和论证的局限,将报应推到了无法验证的过去和将来,增强了理论的说服力。三世报应说与传统的报应理论比较起来,有两个明显的优势:一是说法极为灵活,虽然说报应必有,但不受时间限制,后报之迟可到百生,即无法用现实今生之事加以验证,又不能用已知的历史事实加以考查;二是强调报应无主使,乃由心感于事而生,基于因果关系,具有必然之趋势。这样一种解释系统就比传统的理论更加圆通和高明,在晋宋时代有关因果报应的争论中,佛教一方一般能够处于有利地位也就不足为奇。撇开罗含与孙盛的争论不谈,在慧远、颜延之、宗炳、刘少府与桓玄、戴逵、何承天等人的论争中,反对派或从自然命定论出发,或以传统的儒家王道政治为基础,或以经验或科学的验证为标准,或从形神关系出发(当时还未深入),力图证明因果报应的虚幻不实;但佛教一方的三世报应理论足以驳倒上述任何一种思想的攻击,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其思辩能力和程度远在各家思想之上。
对佛教因果报应争论之双方是不能简单地用是与非来判断的。反对因果报应说的一方有的并不反对佛教,如戴逵即是;有的是站在文化本位主义的立场,坚持本土文化的自给自足,当心外来文化会冲击传统的文化基础,如何承天就是。情况是相当复杂的。论争者本人均是从维护国家政治利益的前提出发这一点是无疑议的。而佛教一方则力图调和佛教的出世主张同儒家治世精神的矛盾,以“方外之宾”的身份来协助王化,此又为任何狭隘的文化观所难作到。实际上,就政治作用和社会功能而言,佛教的因果报应说的价值是非常巨大的。它指出人的命运是人的思想行为(业)所造成的结果。在一个人们无力把握自己命运之时代,它无疑给人们提供了一线改变个人命运的希望,并促进人们为此希望去积极行动。这为传统的儒家和道家中的任何一方所缺乏,故足以弥补传统学说之不足。
还有一点,佛教的因果报应、生死轮回的说教,在当时的条件下无疑更加“合理”地解释了现实社会中贫富贵贱的不公平性,这对于社会的安定是有巨大的作用的。因果报应说对社会各个阶层的每一个人都具有同样的道德约束力,它让人避恶趋善,讲求人生的完美和道德的高尚,追求来世的善报。这种宗教上的道德理想无疑会弥补世俗教化之不足。早在三国时代,来中土传教的西域高僧康僧会就曾经同吴主孙皓讨论过这样的问题,康僧会强调佛教因果报应说具备“备极幽微”之特征,认为“儒典之格言”可比于“佛教之明训”。(《高僧传·康僧会传》)
佛教的因果报应是不是真实的存在,这同上帝是否存在一样,本身就不是一个能用科学解答的问题,而是一个信仰问题,同时还是一个政治问题。我们看到,像何承天那样的反报应论者,尽管能够把握当时最科学的手段和思想,提出判断真理之二重标准,以冲击佛教的报应说,但仍然驳不倒佛教。除了佛教方面在理论上的建树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当时的社会上层也接受了这个理论。在有关《白黑论》和《达性论》的争论中,当时的宋文帝曾密切关注着事态的发展,后来明确地站在了佛教一边。他说:“颜延之折《达性》,宗少文之难《白黑》,论明佛法汪汪,尤为名理,并足开奖人意。”(《弘明集·答宋文帝赞扬佛教事》)何尚之也斥责何承天、慧琳为“愚暗之徒”,赞扬佛教有济俗助政之功。这些正是佛教因果报应说在中土能够长期流行不衰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