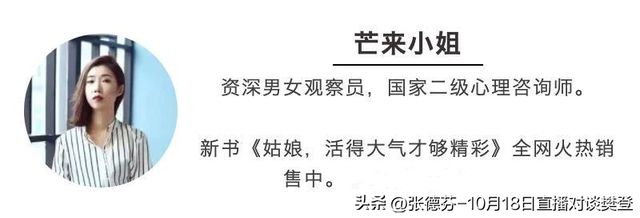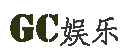是坏情绪啊,没关系纪录片:6种负面情绪人生与3个穿越苦难的真实故事
最近有一部纪录片《是坏情绪啊,没关系》讨论度超高,很多人边哭边看:
“对的,对的,感觉我的内在世界都被呈现出来了”;
“我也是这样的,看着别人一样好治愈啊,我不是异类”;
“原来我很难讲的东西,是这些坏情绪啊,呜呜,完全被表达出来了”;
无数人表示自己仿佛被看见了,也更了解了自己的情绪模式。
纪录片短短6集,每集都呈现了被情绪折磨的群像:
6种被负面情绪裹挟的人生,情况糟到不能再糟。
然而,当事人却凭借成长和支持,创造了柳暗花明的转机,顺利走了出来。
他们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我们又能从中得到什么启发呢?
希望这3个穿越苦难的真人真事,能为你找到穿越坏情绪的答案——
“穿越恐惧的关键,是正视恐惧源”
@李悠扬妈妈
父母最难的阶段,要数儿女生了场大病。
高二的女儿在操场上割腕了,班主任目睹了这一幕,之后,女儿被诊断为重度抑郁症,也不能上学了。
为了让孩子康复,我倾尽全力:
给她熬滋补汤,全程医院陪诊,给她写无数自白信,说我有多爱她……
但孩子并没有因此好起来,还对心理医生说:
“我妈心理很不健康”;
“她尖酸刻薄”。
试问:哪个父母经得住儿女这种对待?
我实在承受不住了,哭着祈求孩子:
“我真的很有压力,你能不能理解理解我?”
“如果不能,能不能起码对我有点感恩?”
“我想得到你的温暖和支持。”
她说:“对不起。”
然后转头就走,留我一人原地痛哭不已。

我完全意识不到当一个大人向一个有抑郁情绪的孩子求助、宣泄情绪,会对孩子造成怎样的伤害。
我只能看到自己的痛苦——
这两年,我经历了妈妈去世、经济拮据、女儿生病。
每天回家前,我都会在车里先哭一场。
孩子对我说:“我也想给你温暖、给你支持、给你力量,但是我做不到,我不想面对你。”
听到她这番话,我的心仿佛被重锤狠狠击中,整个人瞬间僵住。
这份痛到极致的触底反弹,逼着我回看自己的情绪。
然后我看到,我爱女儿的方式,藏着我内心深深的恐惧。
这份恐惧一直在潜移默化传染给女儿,加重了她的抑郁症。

比如:
在恐惧的促使下,我总会否认她的情绪,在她告诉我想死的时候说:
“你不要往这想了,想一些更光明的东西啊!”
我总会对抗她的情绪,在她告诉我她不舒服向我寻求帮助的时候说:
“你别跟我说,你气我。”
当我看清这一切,我开始真正面对内心的恐惧。
这时我似乎变成了一个温和的观察者,静静地看着恐惧,而不再像从前那样被它控制。
我主动问女儿:
“你的这些焦虑压力,其实有些或大多来自于我是不是?
如果我愿意去改,是不是你的压力就会越来越少?”
答案是肯定的。

于是,当女儿捧着被自己撞坏的后视镜,战战兢兢地怕我发火时,我笑着说:“用透明胶带一粘就行了。”
当丈夫出远门忘了拿外套,紧张地等我发火;
女儿也在旁边一声不吭,等待我爆发时,我一笑了之:“没有拿好啊,一身轻松。”
孩子明显轻松、快乐了很多。
我开始明白,父母的爱若被恐惧裹挟,只会给孩子带来伤害。
唯有直面内心恐惧,以正确方式表达爱,才能为孩子驱散阴霾,重迎阳光。
“穿越悲伤的钥匙,
是给自己多一点爱”
@阿睿
小时候,爸爸把我关屋里写作业,看到我没写,拿铁戒尺别开窗爬进来,骑在我身上狠狠揍我,打完之后他说:
“以前都给你一分钟上厕所,现在你挨了打,给你五分钟。”
或许每个青春期的女孩都有过感到悲伤、痛苦的阶段,但对我来说,这个阶段特别长、特别黑。
因为有个这样的爸爸,我恨透了我自己。
我开始憧憬爱情,期待有天“白马王子”能救我逃离苦海。

高一时,一位41岁的男老师夸我、带我玩、带我去他家里……
我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十分懵懂,直到上了高三,我才意识到这是“不伦”。
这个认识,给了我前所未有的绝望——
曾视为救命稻草的人,在这一瞬间露出了肮脏、恶心的真面目,我感觉全世界都在伤害我,都背叛了我。
这样的世界,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我开始自虐,两次吃安眠药寻死,但没死成。
回想起来,我或许不是真的想死,只是想用“求死”来缓解痛苦。
在那之后,我开始尝试其他缓解痛苦的手段——给自己“造梦”。

我想象了一个积极开朗的玩伴“小鱼儿”。
每当我觉得自己很悲惨,写信给他、与他说话就会让我心情好一些,也让我鼓起勇气和老师断了关系。
我还收集了各种植物和种子,腊梅、含笑、紫荆……把它们堆满房间。
看着这些植物的时候,我想:
给植物一点点爱,它们就可以生长得很好,那么给我自己一点点爱,我是不是也可以生长?
这个想法让我怦然心动。
于是,我开始联系了童年时期玩得好的朋友;
主动接受专业的心理治疗,一边打工挣治疗费,一边学习、写论文,每天都过得很充实。
偶尔我也会想:如果没经历那些糟糕的事,我是不是能考上更好的大学?
每当这个念头浮现,心中便会涌起一阵难以言说的惆怅。

然而,我的心理咨询师却用温和而坚定的话语点醒了我:
“前面经历那么多苦,不能白苦,抓住机会好起来,让自己的功能发挥得更好。”
是的,过去发生的已经发生了,不可改变,但也不能白白发生,我把它们化作“绘画”这项宝贵的功能。
我开始用“画笔”编织新的梦,引领我一步步走出黑暗,走向重生。
“穿越厌恶的捷径,
是接纳真实的自己”
@雯雯父亲
不知道你们家中,夫妻俩是否也有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
作为父亲和丈夫,我是唱白脸那个,我整天对着女儿笑盈盈的,从来不表达负面情绪。
然而,在我的用心呵护下,女儿却最厌恶、不信任我。
她在学校遭遇霸凌,不愿跟我说;
她把我关在家门外,还把我拉黑了不让我进门,认为这个家没有我会更好;
她得了神经性厌食症,体重只有34公斤,我努力照顾她,她却说,“我宁愿死,也不要胖。”
当心理咨询师问我对此内心有什么感受,我说:“我就像个多余的人。”

我一直以为,把真实的情绪藏起来,唱好“白脸”,女儿就会喜欢我,结果与我的期待完全相反。
尽管我做了很多努力:放下工作全身心照顾孩子,变着花样给孩子做饭,不远千里带孩子去上海医院治病……
或许,“唱白脸”只是我的借口,我厌恶真实的自己,认为真实的情绪见不得人。
因为我并不喜欢做这些事,我想着或许这就是为什么,女儿也不喜欢我陪着她吧。
毕竟,那种浑身不自在的状态,即便我费尽心思佯装和善,女儿依旧能够敏锐地察觉到其中的异样。
这中间的不协调与异样,就仿佛是在我和女儿之间竖起了一道无形的屏障,将我们隔开。
即便我缄口不言,也能被女儿捕捉到。

有时,我也压不住越憋越高压的真实情绪,会不受控制地爆发出来——跟老婆吵架。
每当我和妻子吵架,孩子总会帮我说话,我本以为这是因为她更爱我,
后来我才知道:她只是更害怕我情绪失控。
我猜,女儿大抵是很讨厌我的,所以无论我怎么照顾她,她都不愿意好起来;
但医生说:她是在用伤害自己,使我们夫妻拧成一股力来照顾她。
这时我才知道,很多时候,父母眼中孩子所呈现出的“问题”,实际是孩子在某种情境下解决问题的方法。
孩子就像一面镜子,他们表面上展现出的种种问题,往往隐晦地映射出父母身上存在的某些问题。
就像女儿,她其实不懂什么是“厌食症”,她只是觉得:这样一来,爸爸妈妈就不会离婚了。
因为他们有共同、一致的“矛盾”要联手解决。

我逐渐开始理解女儿为何厌食,也开始直面自己一直以来对自己的厌恶与不接纳。
于是,我开始学着坦然告诉孩子:爸爸累了,做不动饭了,我来教你,你自己做吧。
孩子学会了做番茄炒蛋,她很高兴,还对我说:
“以后我不会再不吃饭求关注了,我就希望自己的内在能高兴点。”
这何尝不是我的心里话呢?
孩子病了,父母也该一起治病,当我终于看到并接纳真实的自己,我终于如愿以偿地看到孩子的笑脸。
三个故事,三种穿越惧、悲、厌情绪的方式。
他们将生活给与的恶果照单全收,在一切发生后,活成自己该有的样子。
这何尝不是在告诉我们:生活本该如此。
最后,送给大家一首海灵格的诗《我允许》
我允许任何事情的发生。
我允许,事情是如此地开始,如此地发展,如此地结局。
因为我知道,所有的事情,都是因缘和合而来,
一切的发生,都是必然。
若我觉得应该是另外一种可能,伤害的,只是自己。
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允许。
我允许别人如他所是。
我允许,他会有这样的所思所想,如此地评判我,如此地对待我。
因为我知道,他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在他那里,他是对的。
若我觉得他应该是另外一种样子,伤害的,只是自己。
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允许。
我允许我有了这样的念头。
我允许,每一个念头的出现,任它存在,任它消失。
因为我知道,念头本身本无意义,与我无关,它该来会来,该走会走。
若我觉得不应该出现这样的念头,伤害的,只是自己。
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允许。
我允许我升起了这样的情绪。
我允许,每一种情绪的发生,任其发展,任其穿过。
因为我知道,情绪只是身体上的觉受,本无好坏。
越是抗拒,越是强烈。
若我觉得不应该出现这样的情绪,伤害的,只是自己。
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允许。
我允许我就是这个样子。
我允许,我就是这样的表现,我表现如何,就任我表现如何。
因为我知道,外在是什么样子,只是自我的积淀而已。
真正的我,智慧具足。
若我觉得应该是另外一个样子,伤害的,只是自己。
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允许。
我知道,我是为了生命在当下的体验而来。
在每一个当下时刻,我唯一要做的,就是:
全然地允许,全然地经历,全然地享受。
看,只是看。
允许一切如其所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