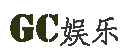易烊千玺新片小小的我深度解析:脑瘫少年的内心世界与家庭情感
馆馆
继《送你一朵小红花》之后,易烊千玺时隔四年再次出现在跨年档带来了影片《小小的我》,两部电影在题材上虽然有相同之处——都聚焦于患病少年、家庭和爱情,但不同的是对人物内心的呈现力度。
《小小的我》用生活化的视角讲述了一个并不常见的角色,刘春和。他八个月时不幸确诊脑瘫,脱力的肢体、不时抽搐的面庞、口齿不清的发声伴随着他的长大。在旁人眼中,他像是一个“异类”,就连妈妈也总将他视为小孩,哪怕已经20岁了还是“一举一动都必须听妈妈的话”。剧情核心正围绕这个关键点开展:刘春和的智力与常人无异,而当一个健康的大脑被困在了羸弱的身躯里,越清醒反而越痛苦。

要塑造这样一个角色,首先必须去掉“我”。演员不仅需要抛开演员本人身体健全的“我”,还需要全身心变成刘春和——手指弯曲成诡异的形态、上下楼梯打绊的脚、努力矫正但依旧含混的语调;再重新塑造“我”——刘春和精神上敏感孤独又顽强的“我”。因为长期不被人所理解,刘春和最渴望得到的是“平视”。他希望无需因为他是残疾人就过度地怜弱和同情,只要被当成普通人公平以待就已经是他梦寐以求的生活。
电影对戏剧化的平衡处理得很温柔,有几处本可以放大成矛盾冲突的地方都被轻轻放过了。
比如,第一次独自走过绿灯且没有超时后,刘春和有个回头一笑的动作。初看会以为他在回望刚刚走过的路,为自己的成长而高兴。直到后面他淡淡地透露,早就知道外婆一路跟在他身后,才恍然大悟那一笑原来不是成功的喜悦,而是给家人的宽慰。外婆悄然的关心被他理解并接纳了,祖孙俩都在用自己的方式默默地保护着彼此不受伤害。
又比如,刘春和努力面试博得了咖啡店的工作机会,入职后却听到别人说“要不是为了减税,谁会聘他”。但是刘春和并未因此而发火,只是继续配合着店长的爱心活动。这份工作对他来说,重要的不是店长的发心善意与否,而在于有了这份工资,有了可以独立挣钱的能力,他就获得了被当成独立的人看待的尊严。
再比如,妈妈怀孕后始终瞒着刘春和,只说要出门住几个月。刘春和似有所觉却没有追问,甚至在某天看见妈妈午睡露出了孕肚后也只是默默帮她盖上了被子,继续装作不知,维护着妈妈不想捅破的窗户纸。
《小小的我》的故事从刘春和出发,镜头也始终萦绕着一股沉静感,所有情绪都更向内收敛,哪怕最激烈的戏份也爆发得无声无息。
观影结束后,观众们对电影的争议大多集中在刘春和与雅雅的感情线上。他们的相遇本来就有很强的偶然性:初次见面雅雅的飞盘飞向了刘春和,刘春和努力许久也无法拾起飞盘,于是雅雅自己捡了回去,两人就此相识。开放式公园容纳了大学毕业后赋闲在家的雅雅,容纳了退休歌舞团,也容纳了被外婆临时拉来学鼓的刘春和。所有的群体都可以在这里和谐共处。
直到雅雅第一次进入刘春和卧室,私密空间的深度相处才暴露出人与人的差异性。有段对话是雅雅惊讶于刘春和的藏书,她问他一书柜的书都看完了吗?刘春和以问代答:“你衣柜里的衣服都穿过吗?”这么问是因为刘春和的衣服很少,买什么都由妈妈决定,所以在他的概念里,衣柜的衣服肯定是都会穿的。但雅雅的生活富裕自由得多,于是理所当然地回答:“没有啊。”刘春和只好重新回应“我都看过”。这是很小的一处两人相处的参差,却也折射出二人爱好、家庭环境乃至人生体验的截然不同。
有人不理解雅雅的主动靠近又悄然离去,但剧本里交代过雅雅接近刘春和不单是出于有趣或好奇,还因为她学的是人类学专业,对特殊群体的心理和生活有着强烈探索欲。在探索的过程中,她后知后觉刘春和有了超出她掌控范围的心动,所以才最终犹豫并退缩了。这种有目的性地接触和突然离开,当然对刘春和造成了感情上的伤害,但从雅雅的视角出发,她从始至终并没有故意玩弄感情的意图。相反,她的出现让刘春和难得地感受到了被看见、被尊重,一如她永远明媚的服饰和笑容,成了刘春和灰暗人生中鲜有的亮色。
另一处妙笔是刘春和与退休歌舞团老人们的互动。由于许多老年人不会用智能手机,身边又缺少年轻人可以求助,刘春和恰好可以帮助他们把手机的问题一一解决;刘春和原本不想打鼓,在被拉来凑数强行要他学鼓的过程中,也体会到了被人需要、收获快乐的情绪正反馈。这种互相帮助、和谐共生,是创作者期待的更美好的社群生活,也呈现了比脑瘫患者更广范围群体的困境。
跨年影片《小小的我》毋庸置疑是一部煽情而催泪的作品,但这份泪不是为苦难而流,更多的是为刘春和重获新生而感动和欣喜。在这部电影极尽温柔的表达里,我们看见了被忽视的人,也拾回被遗忘的爱。而在影片最后一声声“干杯吧朋友”的祝福声中,刘春和迈向了更宽广的未来,我们也在倒数中走向了崭新的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