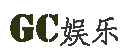贾樟柯:怀旧其实是一件好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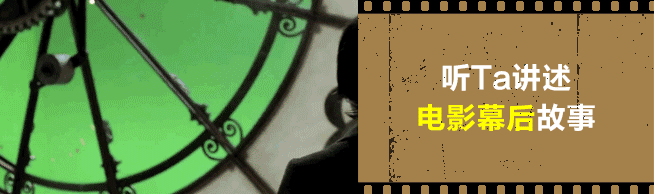
本文受访者为导演@贾樟柯 文章内容根据采访资料整理
时隔六年,我们终于在大银幕迎来了贾樟柯导演的故事片新作《风流一代》。
这部新片对于属于贾樟柯电影的观众来说既熟悉又陌生,熟悉的是那些经典的 视听元素和汹涌的时代背景,陌生的则是这是一部历时22年创作的影片。

从世纪之初的狂欢气氛,到高速发展的剧变时代,再到突如其来的特殊时期,在这部新片里,我们再次看到了贾樟柯用镜头书写的社会变迁和情感流转,也以此重新回顾“贾樟柯宇宙”下的时代痕迹。
本期【大咖讲述】,我们与导演@贾樟柯聊了聊《风流一代》创作的心路历程和幕后细节,更深一步了解影片背后的故事。

Q1:我想拍一部游历式的电影
小万:我们知道影片的创作历时20余年,为什么会采用了这样一种创作方式?
贾樟柯:《风流一代》这个电影最早是从2001年开始拍摄的,那个时候这个影片是叫做《拿数码摄影机的人》,因为那个时候是千禧年代嘛,这个新世纪的头几年被称为千禧年代。那个时候社会氛围非常具有活力,到处是要出去闯的人,整个就是一个狂欢气氛,唱歌跳舞啊,人和人之间的这种包容性很大。
你看电影中经常人们聚在一起聊天、跳舞,你会发现生活中间的这个弹性很大,所以有非常有能量,有激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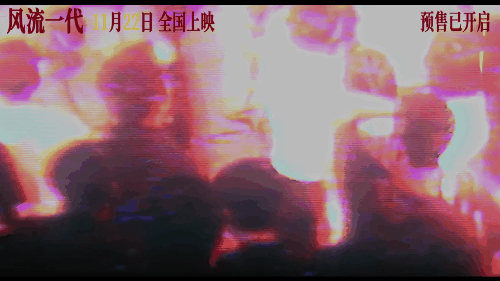
我在当时在那样一个氛围里,就特别想拍一个有历史的电影。什么是有历史的电影呢?就是它不像传统的故事,是我们预设好一个故事,拍摄是由文字到影像的一个转化。
我想在这种游历式的拍摄中遇到不同的人和事,然后再带着演员去即兴地构思一些剧情,最终形成一个叙事,因为这是电影早期非常活泼的一种形式,当时就这样开始拍《拿数码摄影机的人》。
但我们拍了两三年之后,我觉得一直没有一种心理动机能够让它停下来,我觉得没完成这个电影,所以断断续续拍。比较集中在这个01年、02年、03年,然后这个05、06年,然后12年,这些年代在拍摄,拍摄了这么长时间之后,也没有去处理它。

一直到2020年,我突然觉得有一种心理动机,我觉得我该结束这个电影了,因为好像那个时候生活发生很多变化,因为正是特殊时期嘛,大家都在家,出行也不是很方便,你就觉得一个快速变革的人裹挟其中的这么一个时代,他戛然而止了。
包括情感方法,人的生活的具体的形态也发生变化了,就是这个,我觉得该终结这个电影了。我想完成一部最终的电影,就是讲我们从千禧年代怎么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所以它并不是一个怀旧电影,虽然它充满了可以让我们怀旧的元素。

另外一方面,我想拍一个非常沉浸式的体验的电影,除了我们看这个男女主人公他们的这些爱情故事之外,也去感受那个时代是一个什么样的气息。
我本人就是看到01年的时候,特别有感触,你看到那个网吧里的电脑,看到那个墙上还是旭日升冰茶,然后看到满街的夏利汽车。夏利汽车现在我们完全找不到了,那时候就满街都是啊,都充满了这种唤醒我们的记忆,复活我们记忆的这些元素,而这些元素,它不单是一个元素,它是我们的情感载体。

比如说我看到那个夏利汽车,我就老想起我大学毕业时候,我同学喝多了,我就把他扶上一个夏利汽车,去了北医三院。那个车,我的第一印象就是送同学去医院,它都有我们的故事在里面。
那之所以在电影中,就是把它凝聚成01年、06年和20年这几个段落,一方面就是你真的拍了这么20多年,那需要多漫长的一个篇幅你才能完成啊,那时间一定需要是有跨越的,它是一个处理20多年时间应该采用的一个跨越式的一个结构。
小万:经历了这么长时间的拍摄,有大量素材,那您是如何确定前两个片段的时代的,为何是2001年和2006年这两个节点?
贾樟柯:之所以选01年,确实就是因为千禧年代那时候开始拍,这是电影最早的起点,而且那个年头也是有非常重要的影响我们的事情在发生,北京申办奥运会成功,我们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这是大的,还有很多小的,我刚才说的那是一个都要闯的年代,社会开始有活力的年代。

那06年呢,那就是经济高速发展到一个阶段,背后有一个巨大的事件,就是三峡工程啊,三峡工程它一方面是中国经济实力的体现,我们改革的一个结果,因为有财力了,可以做这件事;
另一方面,它又影响了千家万户,影响了中国的经济,影响了几百万个家庭。他们要移民、要迁出,那是一个巨大的变革的场景,我很迷恋这个场景,《三峡好人》已经表现过,但在同时期,在这个电影中我也拍了很多东西,我还想把它再呈现出来。

《三峡好人》
那么还有一个,其实在人物的变化中,一个二十四五岁的女性到了三十岁左右,过了五年之后,我觉得就是她要面临很多真实的生活了。要考虑婚姻的问题,家庭的问题,情感要明确,那她到了一个人生需要清晰的一个年代,所以它也是人物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点。
可能年轻时候沉浸在爱情里,就是打打闹闹或者说互相伤害,但是到了再过四五年,确实要做一个确定了:要不要结婚、在哪儿生活、以什么为业,生活要安顿下来,所以就是从青春到了走出青春的一个年代。

这之后就是当代,因为那之后在剧情中,显然他们就分手了,然后你就可以知道,就人生就分叉了,一个那样生活,一个这样生活。到当代就是一个分叉,之后他们再次相遇,相遇带来他们这些年的所经历的事情的想象。所以既是一个处理漫长时间需要的跳跃,也是这个人物人生过程中非常重要的几个节点,再一个也是中国社会具有非常多的影响我们生活的信息的一个载体。
Q2:我们对于世界的感受就是碎片的
小万:影片中男女主人公的故事其实有大量留白,叙事性并不强,反而是作为背景的时代有更清晰的展示,您怎么看待这两者的关系?
贾樟柯:我觉得他们应该是融入到一起的,因为实际上在剪辑的时候,我们最初的几个版本都是强叙事的。因为我们的素材足以支持强叙事。其实最初一版是顺序的,就是两人相爱,然后他们怎么一步一步发展,他们之间有哪几次回合的纠缠,然后是什么导致了男的要走。
这些都是有素材支撑的,那讲完这个我总觉得它好窄好窄,就是你讲得再热闹,它也永远是一个我们讲了无数遍的爱情故事,而且我们的视点会放得很窄。那么广阔的一个世界,似乎只有这么一点点事情是最焦点的。

所以我就又改了一个方法,改了一个倒叙的方法,就像美国往事一样啊,等于是把当代拍的放在前置,比如说斌哥在上台阶,然后他老了,走路也不方便了。他一回头,哇,想起那个时代,巧巧在那跳舞。空间没变,人变了。
我刚开始觉得不错,挺煽情的,挺有这种怀旧感的,但是我觉得又过于感伤了,它还是一个强情节,虽然你时序打乱了。但我总觉得表达不了我的感受,也提供不了我的一直想有的一种创造一种新的观影感受的那种要求,它总是一种我们习惯了的一种观影体验。
但我希望有一个更加开放性的,你能沉浸其中,无论是沉浸在男女主角的故事里,还是沉浸在他周遭的生活里,都能沉浸其中的作品。你也能游走,你也可以游历,你也可以运动起来。

那我就否定了这两种剪辑方法,再寻找一种新的叙事方法。那这个叙事方法本身就是有一个故事主线,这个主线在,然后这个人物在,但是在到达这个叙事终点的这个过程中,我们会经过非常曲折的路程,看到不同的时代面貌,勾起我们非常多的个人的记忆,情感。因为我们一直说沉浸式,所谓沉浸式的电影,它并不单是说你的音响是不是ATMOS,是不是包裹的这种全景声还是什么样。
所谓沉浸式是你提供的试听能够具有一种支撑沉浸的丰富性,就是在线性的叙事的同时,展开一个空间的拓扩展,让我们看到更多的人和事。当你这个视野广阔之后,我觉得对于我们时代的记忆来说,就能够带给我们一种比较清晰的整体印象。

小万:所以我们看到那些看似和主线故事无关的画面,其实营造了整个时代氛围和时代记忆。
贾樟柯:对,其实他们都有关系。所谓有关系,就是说这是他的生活,他们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他们是互相塑造的。所以我觉得就有点像量子物理,我当时在剪辑时候确实在想这个问题,有一次我跟朋友聊,他说你别瞎拽了,怎么还有量子物理。
我说真的有,因为我们传统叙事其实是万有引力的思维,就是直接的因果关联,层层推进的叙事链情节链。但是这种描述世界的方法对于我们这个目前碎片化的生活是很难有效的,我们拼命地提炼提炼,最后把这个世界又描述成一个这样的情节链。

但我们真实的感受是什么?真实感受是,甚至我们都没有敌人,我们都没有什么因果,在我们身上没发生什么事儿。但是我们怎么就进入不同的处境?怎么解释这种世界?量子物理可以解释,因为世界万物都有关联啊,他们存在,但是关联不是因果式的,他们是一种隐秘的、说不清楚的方法,在一个纠缠之中,产生了这个世界的改变影响。
而且我觉得可能每一代人的生活记忆都是碎片化的,不是说我们有了互联网,有了这么多短视频,我们才碎片化,你就是去访问一个八九十岁老人,让他回忆抗战、回忆新中国成立,回忆他经历的几十年,也是碎片化的。
那我们自身的记忆方法和接触这个世界方法就碎片化的,那我觉得可不可以就是用一种方法来继承下记忆跟生活的碎片化,又建立起这些碎片化的人跟事、场景之间的内在的有机的关联。

这个是我想做的事情,我总觉得,电影的改变一定是随着我们的感受的改变而改变的,当你有一天发现我们习惯的电影方法已经不能描绘我们的生活,不能描绘我们真实体验的时候,一定是需要你去找一些新的方法出来。
Q3:“风流一代”就是变革的一代
小万:影片片名叫做“风流一代”,但是我们看到影片中的主人公其实并不“风流”,甚至还挺“憋屈”,您是如何理解这个“风流”的?
贾樟柯:这个问题是我在海外、在香港,包括在内地,咱们年轻人普遍会问的一个问题,说你为什么用“风流”这个词,这不是个好词。 其实它是一个历史名词,就是在70年代末开始有了“风流一代”这个词,那就好像之前文学史上有“垮掉的一代” “迷茫的一代”一样。
70年代,有个直接原因就是那时候开始改革开放了。 开始改革开放之后,有一首诗那时候家喻户晓,叫《风流歌》,是诗人纪宇写的。 那时候它火到什么程度,广播电台、所有的集会、文艺演出,都要朗诵这首诗。 因为这首诗的火爆,就形成了一个词,叫“风流一代”。 现在还有一本杂志,年轻人的杂志,不是浙江就是江苏的青年杂志叫《风流一代》。

风流一代,它是特指变革的一代。 就是意气风发、不安于现状、渴望改变的一代,叫风流一代。 我在剪辑的时候想起了这个词,因为我觉得他们就是身处在这样一个变革中,他们就是在变革开始的时候成长,然后他们也被变革推动着裹挟着往前走。
所以我觉得哪怕是00年出生的,也是风流一代,因为你的背后,在你甚至不懂事的时候,这个世界在发生着剧变。

小万:您作品中的音乐一直是大家津津乐道的话题,这次除了很多时代金曲的运用,也加入了像五条人这样更当下的元素,在音乐的使用上您有什么考虑?
贾樟柯:首先其实这里面大部分音乐,特别是歌,是那个时候拍到的。 因为就我刚才说的,千禧年代是一个充满了狂欢气氛的年代。 那我们也被这个气氛吸引,去卡拉ok啊,去disco啊,甚至有非常多的街头演出,然后我们拍了很多。
所以那个年代自身,真的就到处充满了音乐,即使没有演出,你走在马路上,两边商场放的都是歌。 不像今天已经声音管制了,因为要环保嘛,不能有噪音。 那个时候还没这个意识,所以是处在一个狂欢里面,你永远生活在歌曲里面。
我们就不自主地拍了很多这样的音乐元素、舞蹈元素,在大部分素材里面都是当时拍的。 另外一部分呢,就是在剪辑的时候我主观地用了一些音乐,包括像万青的《杀死一个石家庄人》,脑浊乐队的《野火》,包括片尾用了崔健的音乐。

我觉得这些音乐我是当主观音乐来用的,我不管他发表的年代,他只要跟我叙事中某一个段落氛围上非常融合,我就可以使用。因为我觉得这个时代不单是我一个经历者,很多艺术家,特别是音乐家,他们跟我经历了同样的时代,他们对这个时代用声音、用音乐也有非常好的描写。
就是比如你一听到万青的《杀死一个石家庄人》,马上回到内陆小城,那种制式化的生活,以及生活在其中人的一种状态。这样的话就形成了整个影片中19首歌的使用。
Q4:换一个角度,这是部有趣的电影
小万:影片中打动我们的,除了戏里主人公之间的故事,还有一部分是戏外两位演员在经历20多年时间里的变化,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这才是故事的重心?
贾樟柯:我相信是这样的,因为他们在这个电影中其实生活了20多年,他们每个在当时我们不予觉察的表情,已经随着时间流逝,演员们的面貌的变化,生活态度的变化,其实是挺震撼我的。
它并不需要太多笔墨,那种无言的……像赵涛,整个影片没有说话,你已经能够感受到她经历的那些岁月; 包括男主角斌哥也是,当他再出场的时候已经中风了,已经非正常地衰老了,就是衰老得很快。 那这些变故,所有东西我觉得我们都能理解,马上我们就理解了他们的不容易,他们中间发生这些事。

所以我觉得这个电影对于院线观众来说,说难也难,说不难也不难。 说难,就是确实我觉得它是一个新电影,不管是一个成功的新电影还是一个不成功的新电影,它总是有挑战性的。
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如果你转换一个频道,是用另外一种理解电影的方法去感受它,它是一个非常容易看的电影,而且会看着赏心悦目。如果你肯转一下频道,就会是一个新的电影天地。
小万:影片因为怀旧被打上了“中式梦核”的标签,您如何看待大家的这种怀旧情怀?
贾樟柯:我觉得在现实生活中怀旧也是一个好事。包括这个电影,我觉得如果能把大家带回到那个年代啊,看到那些我们已经陌生、遗忘但是又激活我们记忆的每一个瞬间,每一个物件,每一个场景,我觉得是很感人的一个事情。但同时我觉得应该怀念的是那个年代的热情跟能量,将这种热情跟能量从21世纪初带到今天来。

如果是这样一种怀旧,我觉得那是非常好的。我们怀旧不是借居在过去的回忆里走不出来,而是说我们要裹挟着过去的能量,我们回到过去,通过《风流一代》,通过这部影片,我们回到22年前。我们重新捕捉那时候的能量,我们来面向今天的生活,我们慢慢获得一种新的能量,我们重新制造一种充满能量的生活。我觉得这种怀旧是非常棒的。
小万:影片中的很多时代背景对于年轻观众来说可能有一些距离,您期待年轻观众如何看待这个故事?
贾樟柯:我觉得对于再年轻的观众,你就算一个18岁的观众,这部电影22年的时间是跟他是有交叉的,最少交叉了是十五六年,对吧。所以就只要大家能够有交叉的部分,你就会理解到之前你记忆的盲点,那是你的一部分,你丢失的一部分。如果我们满怀兴趣地去寻找我们生活中记忆模糊的部分,丢失的一部分,去寻找那些去感受在我们还在床上躺着、还不会说话、还刚开始走路,或者我们开刚开始在幼儿园,外面我们都不知道是什么时候。

你可以找到你的记忆,其实是你的记忆,只是被你的年龄屏蔽掉了,但它属于你的一部分。你可以想象你三岁的时候、上幼儿园的时候,可能外面正在唱那样的歌,外面正在跑那样的夏利汽车,你的父亲可能正在网吧里头上网。
我觉得那其实是属于年轻人的,就是寻找自己的一个密码。我们并不是每个人都掌握自己的密码,通过看这部影片你能感受到,你甚至可能不知道那是一个夏利汽车,但是你可以知道在你还没有记忆的时候,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