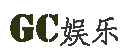迈克·李回来了!等你六年
(2024年10月15日)
随着《残酷真相》的上映,迈克·李暌违六年终于回归大银幕。从影片的开场镜头开始,我们显然又回到了迈克·李的故乡:伦敦的一条现代郊区街道上,有一排即使不算富裕、但也显得相当整洁的家庭住宅,镜头缓缓移过,伴随着迈克·李的长期合作者盖瑞·叶尚的悠缓弦乐。

《残酷真相》(2024)
在接下来的97分钟里,我们将了解潘西(玛丽安娜·琼-巴普蒂斯特饰)和香塔尔(米歇尔·奥斯丁饰)两姐妹及其家人的生活,观察潘西难以自制、漫无目的的愤怒给所有人造成的情感伤害。(香塔尔绝望地对潘西说:「你为什么就不能享受生活呢?」)琼-巴普蒂斯特的表演是影片的灵魂,但正如李的所有作品一样,她的表演也蕴含在层层的关系和观察中——这是演员们几个月来协同即兴创作的结果,她们共同创造了角色及其身处的世界。
如果说肯·洛奇的电影是厨房和水槽类型(厨槽现实主义)的戏剧,那么迈克·李的电影则是水壶、沙发和门廊类型的戏剧;他的电影没有叙事电影的传统,人物的生活从开场到结尾很少有实质性的变化。即使是李后期的年代片也遵循同样的原则,强调人的经验的积累,而正是这种积累构成了我们所谓的社会变革。
在《维拉·德雷克》(2004)中,是战后英国妇女在家庭之外担起新的经济重任时,其生活受到残酷限制所造成的难以为继的紧张局面;在《透纳先生》(2014)中,是19世纪上半叶新文化市场的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新的观看方式;而在《彼得卢》(2018)中,则是通过工业化,一种新的无产阶级生活方式和政治形式的出现。

《彼得卢》(2018)
对于太年轻的观众来说,李的一些作品在公映之初他们都还没出生,而《厚望》(1988)、《赤裸裸》(1993)和《秘密与谎言》(1996)等影片则传达了一种时空感,让人感受到与他的年代片呈现出来的相似的疏离感,揭示了撒切尔主义的反常,以及在国家社会结构扭曲、日趋紧张的情况下为维持美好生活而进行的斗争。

《厚望》(1988)
对于有兴趣了解2024年生活在李所处世界一角的感受的潜在观众来说,《残酷真相》也将起到同样的作用;就目前而言,可以说它捕捉到了构成英国现代生活的冲突与温情的复杂交织。
在影片于今年纽约电影节进行美国首映之前,我通过Zoom与李进行了交谈。
问:《残酷真相》被赞为你在《彼得卢》和《透纳先生》等年代片之后对当代社会现实主义的回归。不过,纵观你的整个职业生涯,历史和当代似乎一直在你的作品中并存。你是否认同《残酷真相》是对你早期电影创作类型的一种回归?
李:我完全不这么看,因为我的所有电影其实都是同一部作品。即使是像《酣歌畅戏》(1999)、《透纳先生》《彼得卢》和《维拉·德雷克》这样明显的年代片,以及《职业女郞》(1997)的前半部分(其背景设定在1986年),我仍然在探讨同样的基本主题,即人与社会。
在某些情况下,我们碰巧选择了历史事件进行探讨,但这并不妨碍它们具有相同的精神主旨:探讨人,探讨我们到底是怎样的人。因此,老实说,除了在最基本的层面上,我并不认为这是一种对不同类型的回归。

《酣歌畅戏》(1999)
问:那么,就你的作品中的相似之处而言,《残酷真相》似乎与《厚望》和《一无所有》(2002)最接近,介于前者的轻松和后者的悲伤之间。玛丽安娜·琼-巴普蒂斯特的肢体表演非常精彩,有时让人感觉很滑稽,但没有说些俏皮话,或是释放、宣泄的夸张动作。在我参加的那场放映中,笑声在影片后半段逐渐消失。现在拍摄关于英国的喜剧是否比你刚出道时更难?
李:生活是喜剧,也是悲剧。这部电影中的喜剧和悲剧元素在我所有的电影中都有体现。毫无疑问,它们都有相似性。显然,你可以说我的电影有自己特定的类型——它们都属于同一个脉络。但我认为,在我拍摄的20多部电影中,没有任何两部是相同的。每部电影都有自己的特点。但我希望我可以说,所有这些电影都以某种方式真实地反映了生活,因此都具有不可分割的喜剧性和悲剧性——因为生活也是如此。
有人说,「哦,你显然是故意把前半部分写成喜剧,然后又改了风格。」我根本没有这么做。我的意思是,这只是发生的事情和你对它的感觉的相互作用。笑声渐渐消失,基本上是因为事情不再有趣了。但我想说的是,在影片中,你所看到的任何瞬间都不止于喜剧——不仅仅是玛丽安娜的角色潘西,而是所有人物及其之间的关系。

《一无所有》(2002)
问:经常被问及电影拍摄时的排练过程和即兴创作,但取景地的选择似乎也是塑造角色的关键。你一般是在什么时候决定取景地的?
李:这是一件非常有逻辑性的事情,真的。我的意思是,你先要创造一个角色,然后让他们存在,构建他们的背景,然后就能清楚地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他们生活在什么样的地方,等等。当然,这不仅仅关乎于我和演员的合作,也是我和演员与美术指导、服装和化妆设计师的合作。我们真的会一起合作,讨论角色住在哪里,角色会有些什么东西。
大多数演员都会告诉你,他们不仅会在片场第一次见到扮演自己角色应该与之结婚40年的角色的对手演员,而且他们还会发现自己所处的环境本应是他们所熟悉的自然环境,而事实上,这与他们的想象完全不同。现在,我们所做的显然是另一个极端。在这部电影中,最明显的是,你可以看到潘西的房子是她的偏执的产物——她对东西、事物、植物和昆虫以及所有其他东西的恐惧,而香塔尔的公寓则彰显了对色彩、光线、植物和欢乐的赞美。
对我来说,这就是取景一直以来的基准。当然,我曾接受过演员训练,读过艺术学校,还上过伦敦电影学院,我是一个视觉主义者,也是一个关注人类行为的人。因此,对我来说,你所说的勘景的乐趣在于如何呈现它的外观,不是装饰性的层面,而是对生活的真实描绘——我们拥有的东西以及我们如何使用它们。

取景地的选择的确至关重要。如果你还记得,在《赤裸裸》中,那些女孩(由莱斯利·夏普、凯特琳·卡特利吉和克莱尔·斯金纳饰演)所住的公寓位于伦敦东区达尔斯顿的一个拐角处,是一栋颇具新哥特式风格的建筑。美术指导艾莉森·奇蒂非常出色,她不停地拿着公寓和公寓楼的参考照片来找我。
我一直不满意。因为我已经有了整部电影的构思,我说:「不,它必须有某种独特品质,不能只是一幢平淡无奇的公寓。」后来,他们又拿来一张照片,——它看起来就像是查尔斯·亚当斯的手笔。这栋公寓坐落在一个尖角上,你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看它,并且有不同的台阶通向它。所以我说,「哦,就是它了。」差不多就是这样。这就是电影制作的乐趣所在。要知道,拍年代片最棒的一点就是创造那些世界的过程令人愉悦。

《赤裸裸》(1993)
问:你在近期的一次采访中提到,为这部影片寻找资金要比《彼得卢》难得多。像现在这样拍摄现实主义电影的条件是什么,不仅对你自己,而且对其他对类似项目和实验性方法感兴趣的导演来说都是如此吗?你对此担心吗?
李:就年代片而言,我们可以对支持者们宣传:这是关于特纳的故事,是关于吉尔伯特和沙利文的故事,是关于彼得卢大屠杀的故事。但通常我会说:「我不能告诉你任何关于它的事情。我不能告诉你这部电影将讲述什么,因为我们就是要通过拍摄这部电影来了解它。我不能讨论选角的问题,在我们拍摄的时候也不要干涉我们。」
多年来,我很幸运能找到这样一群支持者,他们会说:「好吧,好吧,放手去拍吧。」虽然我问过的大多数人基本上都让我们滚蛋。但情况越来越糟了。人们越来越不愿意去支持一个他们无法干涉的项目,他们无法忍受不能根据自己的研究或算法或其他什么东西进行修改。现在我已经摆脱了这种困扰,而且还会继续这样,尽管这意味着预算会很少。但是,年轻的电影人总是会因为这些先入为主的想法而被拒绝,或者被冷落多年。

《彼得卢》(2018)
这些年来,我一直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幸运。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当我们为英国广播公司拍电影时,那是唯一的平台,在大多数情况下,拍电影这件事只会发生在那里。你进去后,他们会说:「好吧,我们不知道你的故事是什么。没关系,这是预算,这是交片日期,去拍电影吧。」然后就会出现各种令人惊奇的创意。这才是我对于新电影人和年轻电影人所真正关心的,无论他们是否忠于现实主义。我希望人们能够以他们想要的方式去探索他们想要探索的东西。
问:《残酷真相》已经在多伦多进行了首映,目前即将在纽约电影节上放映。你的作品非常关注英国及其国族特质,它们在国外的反响如何?
李:它在圣塞巴斯蒂安也放映过了,有趣的是,这三个地方的反响都一样:很多热情和赞赏。包括西班牙在内,这部影片在西班牙放映时配有西班牙语和巴斯克语字幕,反响和其他地方几乎是一样的,同样的笑声,同样的突然沉默。这是个有趣的问题,因为很久之前,在《暗淡时刻》(1971)和《厚望》之间,有一段时期我们想拍故事片却不能拍。

《暗淡时刻》(1971)
那段时间我在拍电视电影和排戏剧,有一次,我去见一位住在伦敦的美国制片人,他是个好人,他说:「我很喜欢你的作品,非常棒,但你永远也拍不出故事片,因为故事片必须在美国成功。而你的电影永远不会成功,因为美国的观众根本不知道它们讲了什么故事。」事实证明,这个预言是完全错误的。从《厚望》开始,我的作品一直非常成功,深受美国观众的欢迎。
问:因为它们都是关乎人性的故事?
李:当然。观众会与影片的实际内容产生共鸣。你知道,我曾经去日本为《秘密与谎言》做宣传。

《秘密与谎言》(1996)
在我去之前,有人说:「你知道,日本观众可能会对一个黑人女人和一个白人母亲以及其他的东西不太适应。」所以我又去问发行商:「你觉得怎么样?」他说:「这是一部非常日式的电影,它关乎家庭、秘密和谎言,关乎隐秘的东西,非常日式。」就是这样。